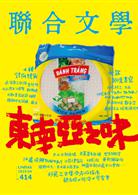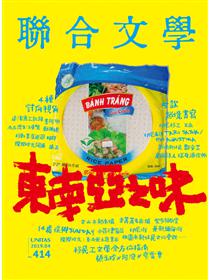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室報告】
年華
執行主編 蔡俊傑
前陣子終於抽空,趁著一個午後騎車上了陽明山,沿途上山的路線暢空無阻,反而是左手邊下山的車潮接連不斷。想著這台機車也是老朋友了,當年剛剛來到這座山上讀書,它也是才新上市的車款,而今僅僅是一般的山路爬坡,也顯得稍微勉強了些。從引擎聲,拉催油門的緊弛回饋,表面氧化褪色的車殼包裹著車體的顫動,輪胎轉動中輾過了那山道上添添補補的凹凸坑洞傳來小碎石滾蹦開來彈射到輪框的聲響,回氣,再輕輕的拉緊油門,感受這老朋友,仍舊協調著整體所能,蓄積著力氣把自己往那傾斜的山道前方送去。
雖然說無法再像青春時那樣追風逐電,想到就給它飆一下,但其實心裡是滿享受這樣的緩慢所帶來的悠晃,用著比年輕當時,更憊懶的速度,徐徐繞過那些熟悉的彎道,樹叢中閃現的俯瞰城市,小小移動的火柴盒汽車一下子就被雜亂的葉叢樹影遮藏,像是收到抽屜裡的玩具那般,再往上走,路旁剩下樹,以及幾乎清空的山路。幾天前的雨下得不甘不願,雲層溫吞飽滿,所幸天空還在,彷彿圍上了洗到灰白的薄布還隱隱透亮。
迎面而來的熟悉氣味,是九月入秋前,白日的熱燥被午後山林間逸散出來的水氣消解,帶點草葉邊沿的腥潮濕氣吹送的風不算涼,但體感知道那確實掀開了貼膚的燥熱。我想起那時在課堂上遇見我的小說家老師,第一堂課晃進來,還以為走錯教室,背包地上一扔,就開始對著我們講那些大小說家的名字,三兩句就先開了二、三十本書單,都是我這從南部鄉下上來的小孩從來沒聽過的。我仍記得那時(想想比現在的我還年輕)的小說家老師對著我們暢談他喜愛的每一本小說、漫畫和電影,談著飛矢論、談著時間,談著那些故事裡的故事(「我說的都是真的!」),談著各種關於小說,或者說,關於創作的可能性。至今想起,那些摻著瞌睡和(老師)翹課的課堂,一直都是我最珍惜的美好時光之一。當時的我想著,原來這就是小說,後來的我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啟發我的,不只是小說,還有「小說家」這樣的角色。
現在想想,也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心裡就萌發了這樣的念頭──我想成為一個寫小說的人。而我仍舊不確定自己是否成為了想成為的人。再後來下山了,幾年幾年輾轉,直到某一次,當我的小說家老師對我說著我也是他的老朋友了,我才發現原來時間早已用各種方式,或早或晚的作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話說回來,十月仍是屬於收穫的季節。青年超新星文學獎舉辦至今已經第十二屆,集合各大學文學獎小說首獎,再次經過徵選出一名首獎與四位優等,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獎項,更是連結更多同世代寫作者的契機。每一年的作品中,似乎也都會看到這些年輕的創作者,藉由各自交出的作品,想像著關於如何成為一位小說家這件事。當然,這些經由各種作品組合,以及不同評審的標準與喜好,從各大學選出的首獎,再進而選出的五篇得獎作品,真的要說,也只能說是其中一個面向的呈現,並無法完整概擴全部。
有時我總會想,那些因為獎的限制,更多沒有被選上的作品,那幾千、幾萬字的,我們自己明白,必須得扎實地花上相對的時間去完成的作品,那其中所乘載託付的期待,或者是坦承,或者是一種完結,或者是其他的什麼。想著那些從獎的指縫間溜出的作品,回到創作者自己手上的那一刻,細數自己曾投注的時間,對於曾想像的那個成為小說家的自己的身影,是更清楚些,還是會模糊了些?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