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意:在國民與民國之間
數次革命的失利不能不使一大批仁人誌士重新思考現代化的出路。“南北議和”的結果使得孫中山也對“君主立憲”認可:“譬如英、奧等國,君主國也,而政治之進步與民主國無異,因君主雖有君主之位,而不能干預政治專制害民故也。”。而袁世凱雖欲專制但也必須進行“開明”式的“立憲”。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在“民意”中“合法”擔任大總統後,出台的盡是些“專制”的條款,而缺少“開明”的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本來,從開明專製到君主立憲再到共和立憲是現代化道路的漸進選擇,但由於中國人“心比天高”,恨不能在一夜之問“民主共和”、獨立自由,於是在“命若紙薄”的情形下呼天搶地、搥胸頓足了。當然,在民眾看來,民意多少有被強奸的成分。可要知道,若是真的根據國情(民意狀態下的國情)思考出路,袁世凱的選擇(至少袁世凱是這麼看)已經夠激進了。平心論之,究竟誰在違背民意、誰在反逆國情,不是單單憑藉目的是否達到來判斷的。再回首,在“民意”、“國民”、“民國”之間至少存在著三重思想的弔詭。而且,隨之而來的“五四”都要切實面對這三重難以解開的困惑。
第一個弔詭便是理想與現實的交錯。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連中學生都曉得辛亥革命的起因。畢竟,孫中山也上書過李鴻章,希望能加快改革速度。但結果只能和戊戌變法一樣,結論眾口一詞:戊戌變法的事實證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先進的人士認識到,只有革命才能夠救中國。由此以來,“自下而上”的共和革命紛至沓來。在傳統功利意識、民主共和情結的催促下,革命黨人自然不會聽取思想界對革命會不會流於“作亂”的忠告。於是,“大風起兮雲飛揚”。不難想像,在連“國民”尚未蛻變為“人”的幼蛹中“試飛”是多麼天真的事情。這的確應驗了馬克思的名言:這種“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
共和國的破滅是“驕囂”之風的證明,捨近求遠只能是烏托邦的幻想。而烏托邦結局的可悲下場又更加激起國民對烏托邦新一輪的企望。辛亥革命之後的接二連三的“革命”使得中國秩序大亂,求“治”心理來得比任何時候都急切。倘若我們懷疑“教科書”的權威,就不禁要問:難道戊戌變法的失敗就真的證明革命是惟一不二的法門嗎?中國一定要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嗎?當然,自上而下的道路是有千年等一回的無奈和時間代價,但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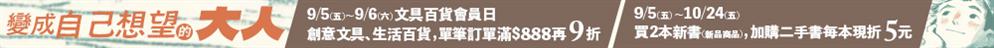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