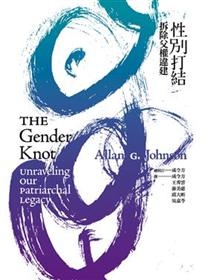★韓國社會學家訪談身心障礙女性,分享難以啟齒的性與愛的生命故事
★分析韓國社會對女性、障礙者以及性慾的三重綑綁
★拆解性別歧視、障礙歧視,挑戰主流社會對「正常vs異常」、「健全vs障礙」、「他者vs我們」等等二元觀點
「其實,我們障礙女性也對性很感興趣啊(大笑)」
「我們的性教育都只在教如何避免被性侵」
「我的夢想是和非障礙者戀愛、結婚」
「媽媽是障礙者讓妳很丟臉嗎?」
「萬一孩子也像我一樣有病怎麼辦?」
「就算生出來的孩子沒障礙,也會被同儕取笑或傷害」
性與愛,是女性最基本的渴望與人權,但對障礙女性而言,卻往往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在社會以「保護」為名的控制之下,戀愛、性愉悅、結婚、扶養孩子等完整生命的渴望,竟成了不被允許的危險行為。
但她們依然勇敢去愛,在不平等的舞台上,以鏗鏘有力的聲音述說她們獨一無二的故事。
韓國學者林海暎在本書中指出,社會的三重綑綁——對女性、障礙者、性主體——如何共同形成對慾望的羞恥結構,並揭露韓國社會對障礙者的歧視已病入膏肓的陰暗面。
她引用影視、書刊中關於障礙女性的情節,交織著真實人物的深入訪談,呈現出一個又一個吶喊著想要愛、渴望掌握人生的鮮明女性圖像。
台灣與韓國、香港其實共享了一個類似的東亞脈絡——儒教的家父長文化、對女性貞潔與障礙的雙重規訓、以及國家對「適當性」的隱性審查。
透過傾聽她們的故事、了解彼此的差異,我們終將明白,「她們」與「我們」看似不同,但其實並無二致。
透過受訪者的身體經驗,林海暎看見儒教父權體制下「保護」與「羞恥」如何同時運作,並看見障礙女性如何在縫隙中創造微小的自主空間。——李柏翰(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簡介:
林海暎임해영Lim, Hae Young
於成均館大學取得社會福利學博士學位。現為Yemyung研究所社會福利學專任教授,教授社會福利學碩、博士課程。
林海暎教授長期關注障礙女性、家庭議題、質性研究,並持續在相關領域進行研究與交流。近期研究成果多為障礙者的性經驗、性暴力受害女性、障礙者照護人員的心理、障礙青少年的撫養等。另著有《脫北者居民與地區社會福利》等。
譯者簡介:
王品涵
專職翻譯,相信文字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現居台北。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暖心推薦(依照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李柏翰│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郝柏瑋│諮商心理師、彩虹樹心理諮商所所長
周月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退休教授、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座教授
陳伯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郭惠瑜│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名人推薦:暖心推薦(依照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李柏翰│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郝柏瑋│諮商心理師、彩虹樹心理諮商所所長
周月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退休教授、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座教授
陳伯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郭惠瑜│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章節試閱
性需求
回顧於2022年5月化為天上星星的電影演員姜受延過往的電影作品時,腦海中閃過令我留下強烈印象的作品《處女們的晚餐》(처녀들의 저녁식사)。這部電影講述三名女人的性與愛故事,分別是享受性愛自由的好靜、與男朋友談戀愛的妍伊,以及完全沒有與男性有過性經驗的順伊。筆者是在社會嚴格要求女性婚前守貞的1970、80年代度過求學時期,緊接著在大學畢業的同時結婚,然後生下兩名孩子。或許是因為如此吧?對於當時像筆者一樣普通的女性來說,這部電影的上映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尤其是當有男朋友的妍伊,以充滿挑逗的想像談論起由她主導與陌生男子的性行為時,那些台詞的內容在當時社會風氣之下絕對是難以啟齒,也不被允許提起的。對當時的社會而言,由女性主導性行為的想像,更是無法想像的挑釁。但對於曾幻想過作為主動主體來掌握性愛體位的女性來說,這勢必啟發了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女性,嘗試任由想像自由馳騁的滋味。此外,電影中關於好靜享受性愛自由、順伊談到自慰的便利性的台詞,無論是當時一般女性視為禁忌的與多名男性的開放性關係,或是對像筆者一樣以性器官為主來理解性關係的已婚女性,這些情節確實難以接受。同時,這部電影就像「打破禁忌」這句話一樣,點燃了燎原之火,激發當時女性想打破社會的性觀念禁忌的潛意識欲望。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男女在戀愛與婚姻生活中,對於性的期望比過往多了許多。女性在給予性快感的同時,也期望獲得快感,並且認為性生活滿足是幸福戀愛與婚姻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任何擁有性慾的女性,無論是年輕或年長、肥胖醜陋、性感美貌、障礙女性或非障礙女性,皆能是想做、能做的性主體。作為性主體的女性,無論在現實或性幻想中,都可以與自己渴望的對象翻雲覆雨,朝著性快感的巔峰展開攻頂的冒險之旅。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女性很難自由、輕鬆地表達與性有關的欲望。當女性向周圍的人坦然且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性欲望時,她就會在瞬間被打上「隨便」、「放蕩」、「濫交」的烙印。
更何況,當「她」是障礙女性時,社會對她們性慾的扭曲刻板印象,迫使她們更難表達自己的欲望,乃至要她們以更極端的方式禁欲。於是,「障礙女性的性慾,被理解為不存在、不該存在的東西,或即使存在,也被認為在性方面是無能的,有的話反而會招來某些危險。另一方面,障礙女性的性慾又被想像成無法自行控制,甚至是會對他人造成威脅的欲望。」那麼,障礙女性實際上作為渴望也能行動的性主體,她們究竟如何體驗對性的欲望呢?
障礙女性表示,她們對於性的需求固然存在,但由於缺乏共同滿足性欲的對象,因此往往沒有宣洩的機會。視障者N,雖無法自由外出活動,內心卻仍渴望透過與伴侶的性關係來滿足性需求。她直到幾年前才開始與現任伴侶交往,在此之前,就算有欲望,也沒有機會排解。在沒有性伴侶的那段時期,她無法被滿足的欲望只能靠夢中的幻象解決。
時常浮現「好孤單、好寂寞」的念頭。我也是人,也是女人啊⋯⋯就算我的眼睛再怎麼看不見,再怎麼沒辦法外出,但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思想。到了現在才有伴侶後,偶爾也會做⋯⋯但畢竟我們都有一點年紀了,不會像年輕人一樣,把所有心思都放在那回事(指性關係)。不過,偶爾得到釋放和完全沒有釋放是不一樣的。以前是因為沒有伴,所以想做也沒辦法做。當然不可能隨便找人做嘛,況且也沒人在我身邊⋯⋯有時候,我會做很多關於男生的夢。就是⋯⋯在睡著的時候,夢到自己做愛。還有像是男生偷偷靠近我,然後做那件事的夢。我也會想要(性關係)⋯⋯但因為身邊沒人,所以只能靠做夢釋放。〔N〕
對於沒有性伴侶的B來說,每次觀賞瀰漫色情氣氛的電影,或在洗澡後見到自己裸體時,偶爾會浮現某種性興奮的奇妙感覺。可是,在沒有對象滿足她微妙的性興奮竄湧的情況下,這種感覺就像是曇花一現的煙霧,遺憾而空虛。至於智能障礙女性J的例子,則是當她看到電視台在深夜播放的成人影片時,自己也會出現渴望建立那種性關係的欲望。然而,在沒有男性性伴侶的情況下,便不可能實現她的欲求。
看色情電影之類的東西時,不是偶爾會有那種奇妙的感覺嗎?我偶爾⋯⋯真的很偶爾會在洗澡或脫衣服的時候⋯⋯看著鏡子裡的我,覺得自己滿美的。當下,就會有想做愛的念頭⋯⋯但我沒有交往中的人,也沒有可以一起做的人⋯⋯就算稍微閃過這種念頭,也無可奈何吧?即便我只是想感覺一下自己是個女人,但也沒辦法,所以這種感覺只會在我的腦海出現一瞬間,然後就消失了。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B〕
電視會在半夜播放有性愛場面的節目。我有時候就會有點⋯⋯老實說⋯⋯有點想做。我當然會想做,我也是女人啊。但沒有男人,我能和誰做?沒辦法做啊⋯⋯總得有個對象才行吧。就算想做,也沒有機會。〔J〕
自我介紹為「母胎單身」的視障女性T,在二十多歲的人生中,從不曾和異性有過輕微肌膚之親。她當然曾在電影中聽過男女纏綿時的興奮呻吟聲,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接觸男性,卻從未對性有過好奇或興奮。T表示,她之所以對異性感覺沒有興趣或性慾,可能是因為從來沒有認識性對象的機會,也可能是自己對性沒有興趣或欲望。
T:坦白說,我沒有任何性經驗。我是母胎單身⋯⋯徹徹底底的母胎單身⋯⋯所以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笑)。很多人都說,過了青春期開始接受性教育後,就會對自己的身體和異性產生好奇⋯⋯但老實說,我對異性真的不太感興趣,也似乎沒什麼性需求。以前會在電影裡聽過性行為時發出的奇怪呻吟⋯⋯但我幾乎不曾有過想做或好奇的感覺。
海暎:您是不想嘗試性,或是根本沒有這種想法嗎?
T:看(聽)色情電影的時候……的確會感覺怪怪的。但我覺得,這好像不會和「不如我也想做一次看看?我想做。」之類的想法連結在一起。可能我真的對那方面沒什麼興趣吧。
海暎:您在上次的訪談中,似乎有提到自己希望和非障礙男性交往的想法?
T:對,如果有緣交個非障礙者的男朋友,我當然想。我想交非障礙者的男朋友⋯⋯不是因為我想發生性關係,才和非障礙男性交往。我是不知道真的有了男朋友會怎麼樣啦⋯⋯但我沒有特別想嘗試性的念頭。連和男生簡單的碰觸或擁抱,我也從來沒有過。畢竟我是視障者,其實經常有機會和男生有肢體接觸,但⋯⋯那是因為我是視障者,肢體接觸當然是家常便飯啊,所以我說的不是這種,而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那種以異性的身分發生的肢體接觸。可能因為我沒有機會吧⋯⋯所以我對異性不太感興趣。也許在生活中⋯⋯曾經產生過那種衝動的感覺,但我從來不曾覺得「咦?這是性衝動嗎?」我覺得自己好像感覺不到這件事。
由口述內容可見,障礙女性表示自己在生活中缺乏認識異性的機會;而缺乏機會是導致她們即使有性需求或性衝動,也無法發生性關係的原因。不過,部分障礙女性對於被當成對性沒興趣、是沒有性慾的人,感到不悅。她們只能在關係親密、自在的的障礙者同儕間,才能討論與性相關的話題,這是必須與非障礙者同儕、朋友迴避的禁忌話題。
以肢體障礙女性P為例,她表示自己至今仍對她在十幾歲時認識的非障礙男性感到強烈的不快。對方不將像她一樣的障礙女性當作可以戀愛、結婚的女人,而是將她們視為「不是女人」,認為不可能跟她們戀愛或結婚,甚至無法想像與其發生性關係。那個男性曾當著P的面,毫不避諱地說他做了一個糟糕的夢,夢到自己與障礙女性結婚。她說,雖然隨著時代轉變,越來越少人說這種話,但也不可否認抱持這種離譜想法的人依然存在。
這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有很多上了年紀的大哥到我們○○院當志工。其中有個大哥⋯⋯我甚至連稱呼他一聲「大哥」都不想⋯⋯那個人對我說:「我昨天做了一個糟糕的夢。」我回答他說:「什麼夢?」他說:「我夢到和障礙者結婚。」我說:「有那麼糟嗎?」他回答我:「很可怕耶!」我接著說:「大哥,你面前的這些人都是障礙者。」「妳們又不是女人。」當時,我只是在內心想「混帳」就沒再多說了……我們那時大概十九、二十歲吧……那是正值漂亮的年紀耶⋯⋯後來,我常會想「居然說我不是女人?」「為什麼不把我當女人?」直到現在,我對那個混帳的發言記憶猶新。時代已經變了,應該沒什麼人會說出這麼莫名其妙的話了吧?不過,我覺得現在還是有人是這樣看待障礙女性的。〔P〕
此外,她也談到自己在某企業工作多年來,多次與同事聚餐、喝酒時發生過的不快經驗。P表示,有時女生們在酒過三巡後,會開始放鬆地聊些關於性的玩笑,但她卻不得不意識到那些同事投向她的眼光,實在令人感到不自在。因此,她總會假借自己有事,尷尬地提早離場。P認為,在以非障礙者為中心的社會裡,即使在大家閒聊性趣與欲望的日常社交場合,障礙女性也會被邊緣化。於是,她說只有在與障礙女性或親近的障礙者們聚會時,她才有辦法自然地聊起性方面的玩笑。
P:就是啊,如果和公司的人一起去喝酒的話,大家不都會在喝了幾杯酒,氣氛炒熱後就開始亂開玩笑嗎?我工作的地方,女生比較多。我做這份工作也超過十年了⋯⋯所以當然也去過不少次聚餐、喝酒的場合。無論是男生或女生,應該都會在喝幾杯酒後,開始聊些色情的話題吧?像是「不關燈怎麼寫功課?」⋯(中略)⋯不是很多這種笑話嗎?是吧?
海暎:是啊,大家多少會在喝酒的場合說這種笑話。女生之間也會。
P:沒錯,我們公司的業務部門有幾名障礙者,但就算是在無意間說出那些話,其他人也會悄悄觀察我的臉色。我後來漸漸察覺到這件事⋯⋯老實說,我也很會說那種黃色笑話啊,怎麼了嗎?對性有興趣的人本來就會愛開黃腔吧?我實在很討厭那樣的眼神。
海暎:對於哪些部分感到不愉快呢?
P:就是「我可以在障礙者面前說這種話嗎?那些障礙者想必對性不感興趣吧⋯⋯也沒辦法做愛⋯⋯」這種荒謬的想法其實都寫在他們臉上。但奇怪的是,我們這些障礙者總是會在非障礙者面前變得畏縮。現在可能比較不會,但以前真的有這種情形。如果感受到那種令人不舒服的眼光,我應該用更多黃色笑話大方回應才對,但當時的我沒有那麼做。畢竟是生活在以非障礙者為中心的社會,像我們這種障礙女性,根本沒辦法在非障礙者面前談論那回事(指性),甚至只能假裝沒聽見、迴避。其實,我們障礙女性也對性很感興趣啊,坦白說,還有很多人超喜歡的。總之,因為這種氛圍的關係,所以我通常都會在第一攤結束就離開,或是隨便找個藉口提早走。不過,等到我們自己(障礙者)的聚會時,或是和障礙者朋友見面時,就會開始大聊沒辦法(在公司聚餐)聊的(色情)話題,包括我在內也是(笑)其實我覺得,關於障礙女性在性與性慾方面的現實情況,大概就像我之前提的那樣吧。
腦性麻痺女性C有語言障礙。她表示,幾乎沒有非障礙者會和身體扭曲的自己開關於性的玩笑。相反地,別人會覺得她談論性的話題很可笑,很可能因此把她當作嘲諷的對象。
絕對沒辦法和非障礙者聊性的話題。像我們這種人,不是有語言障礙嗎?每次和非障礙者說話時,雖然他們努力不要表現得太明顯,但我可以從表情看出他們有多不耐煩。連平常說話都說不好了⋯⋯當然不可能聊什麼性啊。再加上,像我這種情況的人,一講話就會全身扭曲、顫抖。這樣還要開黃腔的話⋯⋯勢必只會被認為可笑。「用那種身體做愛?」、「真是醜人多作怪啊⋯⋯」〔C〕
有性伴侶的障礙女性則認為,她們也想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性需求,但在社會傳統觀念上,這件事並不容易。她們一方面想主動表達需求來滿足性慾,另一方面卻也對伴侶無法滿足自己感到不滿。精神障礙女性Y表示,已婚的她偶爾會渴望與另一半行房。但她擔心萬一向丈夫展現性慾,可能會讓對方誤認為她不夠純潔,所以才不願意直接表達自己的需求。
老實說,我有時候也會想和老公做(指發生性行為)。偶爾就是會想做嘛,但如果女生主動要求的話,好像觀感不太好,讓人覺得有點「好色」。就算想要,也不太好直接開口要吧。我老公對那方面的事,感覺有點遲鈍。每次回家就是倒頭大睡⋯⋯我們做的時候,彼此都滿開心的⋯⋯但我不會說想要,也不會先開口提議。〔Y〕
另一位腦性麻痺女性L則會向情人積極展現自己的性慾,表達對性關係的渴望。L表示,她總是不滿情人無法滿足自己,或對於性方面較為被動,甚至性慾低落。
我經常想脫內褲⋯⋯但大叔(指伴侶)一直幫我穿回去(笑)。我經常吵著想要,他就會用手幫我解決。他現在已經不是喜歡肢體接觸的人了,畢竟有點年紀,加上有些功能也下降了⋯⋯有次,我們去○○玩的時候,住在飯店裡。照護員還特地避開,讓我們倆有獨處的時間。結果大叔只幫我洗了澡⋯⋯就沒有下文了。我很喜歡做(指發生性行為),也渴望濃烈的性,但⋯⋯我在那方面完全得不到滿足。〔L〕
視覺障礙女性D的情況則有別於L,她有時會希望透過與情人的愛撫紓解生活中的緊張,並感受這種肢體接觸所帶來的愉悅與放鬆。因此,D也表示她會主動向戀愛對象提出愛撫、性交的要求。
對我來說,肢體接觸不僅會帶來放鬆的感覺,還很舒壓⋯⋯所以我覺得很棒。我從小就非常喜歡自己的身體被緊緊擁抱、撫摸,我真的太喜歡那種肢體接觸的感覺了。像我一樣的視覺障礙者,和別人有肢體接觸其實是家常便飯。雖然是在有穿衣服的情況下⋯⋯但兩人間偶爾會有些比較親密的肢體接觸,像是摸耳垂、愛撫,這都會讓我感覺我們是一體。當然了,如果是親吻之類的肢體接觸,我只會和有情感交流的人做。所以我有時候會主動要求伴侶「摸摸我」或「我們來做(指性關係)吧」。當我想放鬆、舒壓一下的時候⋯⋯我就會主動去弄他。(笑)〔D〕
障礙女性身為「性慾」這種內在衝動會突然竄升的主體,這股衝動會指向可以協助她們釋放的他人。部分障礙女性僅是因為沒有性對象,也缺乏認識性伴侶的機會,因此她們對於非障礙者將想做也能做的自己視為沒有性慾的無性存在,以及不被當作可以輕鬆分享性話題的主體的態度,感到相當不悅。在這種非障礙者的思想與態度主導的社會,障礙女性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有性的存在。於是,性話題或開黃腔成了她們只能在障礙族群的場合談論的話題,在非障礙者的場合反倒是必須保持沉默或迴避的禁忌。
此外,障礙女性也意識到,在以男性為主的性文化支配的社會,她們若主動展現性慾或尋求滿足時,稍有不慎就會觸動社會文化的規範對她們進行性汙名化。因如她們無法輕易表達自己的性慾或追求滿足;即便她們表達了,但若依然沒辦法滿足,那她們就會把這理解為是必須在內心自行消化的問題。
性需求
回顧於2022年5月化為天上星星的電影演員姜受延過往的電影作品時,腦海中閃過令我留下強烈印象的作品《處女們的晚餐》(처녀들의 저녁식사)。這部電影講述三名女人的性與愛故事,分別是享受性愛自由的好靜、與男朋友談戀愛的妍伊,以及完全沒有與男性有過性經驗的順伊。筆者是在社會嚴格要求女性婚前守貞的1970、80年代度過求學時期,緊接著在大學畢業的同時結婚,然後生下兩名孩子。或許是因為如此吧?對於當時像筆者一樣普通的女性來說,這部電影的上映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尤其是當有男朋友的妍伊,以充滿挑逗的想像談論起由她主...
推薦序
中文版推薦序一
性作為方法——從身體出發,重新想像親密、關係與性權
李柏翰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理事
受訪的智能障礙女性J回憶起她青春期時摸索身體的經驗。她有點靦腆地說:「有時候摸到太酥麻就會叫出聲音,完全不由自主。」那句「不由自主」帶著難以掩飾的羞赧,也產生一種確認自己仍然活著的感受。另一位受訪的視覺障礙女性D提到,她從國中時期開始會聽色情錄音、試著探索身體的反應,即便如今有了伴侶,偶爾還是想「自己來」,因為那是能「取悅」自己的最佳方式。對她們而言,自慰不是逃避關係的孤單行為,而是確認身體與主體性的一種練習。
林海暎教授在《我也想要愛!:障礙女性的情慾、身體與自由》中,透過障礙女性的經驗與視角,重新詮釋對性、愛、情慾的理解,將這些故事置於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之中。她提醒我們,慾望的存在不只是生理現象,更是社會如何界定「誰能被愛、誰能被渴望」的問題。書中有個重要的討論——我們該如何稱呼這些情慾主體?是「女性障礙者」還是「障礙女性」?這兩個用語之間的細微差異,可能折射出我們在性別與障礙政治中的立場與想像。
對多數障礙女性而言,社會仍以「保護」為名排除她們的身體,使性被視為危險、慾望被視為不相稱。她們在戀愛時被警告「那樣很危險」,在婚姻裡被要求「乖巧節制」,甚至在母職中被質疑「是否有能力撫養孩子」。曾懷孕但因腦性麻痺造成身體疼痛的L最後不得不終止妊娠,但那個過程才讓她意識到社會如何將障礙與母職對立起來,她的選擇不被尊重,醫療體系也缺乏理解與支援。如作者指出的,這不僅是醫療歧視,更是儒教父權文化對「母親」角色的道德化框架——女人必須犧牲、必須堅強,但若是障礙者,則被預設了欠缺成為「好母親」的能力。這樣的矛盾,在韓國、台灣乃至整個東亞都再熟悉不過。
這也構成本書反覆追問的出發點:障礙女性如何在矛盾中追求並實踐親密與關係。書中收錄了幾對選擇非婚同居的身心障礙情侶。他們試圖在現實空間中實踐愛與親密,卻發現這樣的生活在制度上幾乎無法被承認:申請住房補助會被拒絕、在醫療場域無法被視為監護人、分手時也沒有任何法律保護。這些細節讓人看見,當兼顧愛情、親密、陪伴與照顧的關係被置於「合法/不合法」的框架裡,障礙者不僅要持續協商物質性的各種限制(包括自己的身體、外在的環境、生存的資源),更要面對國家與「健全」社會的雙重否認。
林海暎的文字克制而溫柔。她不浪漫化,也不哀嘆;她讓這些聲音保持原貌,並以社會學的分析指出,韓國社會的三重綑綁——身為女性、身為障礙者、身為性主體——如何共同形成對慾望的羞恥結構。這本書的倫理核心或許就是要我們正視並理解差異,而這並非為了證明彼此相同,而是為了讓不同的主體經驗都能被視為理所當然,且看見它們都是相互構成的的存在。
在閱讀這些故事時,我一直想起陳昭如的《幽黯國度》。那本以人類學方法完成的深度報導,記錄台灣多位障礙者在親密關係中的掙扎與自覺,在這些故事中,「身體界線」的概念是複雜且關係性的,無法被一刀切的公/私領域、個人與他者、體貼與侵犯、需要與想要。如《我也想要愛!》,它們都在扣問一個簡單卻深刻的問題:為什麼社會願意談「照顧的愛」,卻總避談「慾望的愛」?當「照顧」被視為唯一正當的身體關係時,障礙者就被鎖在「無法慾望」的困境裡。林海暎在韓國的研究進一步揭示,慾望的政治如何決定誰能擁有身體自主(不過什麼是自主呢?)、誰能說出愛(又怎麼才算適切地表達?)。
在香港與台灣,《有愛無陷》及《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則從行動現場出發。作為「手天使」志工十年的紀錄者,易穎華以細膩的筆觸寫下她陪伴障礙者探索身體與慾望的經驗。不只是記錄,她也不斷反思並反問讀者「協助/支持」與「被協助/被支持」之間的權力關係與倫理意涵。正好與學術研究相互對話,殘疾情事並不以理論為重,而是透過十年的陪伴展現「性作為關係」的倫理實踐,在相互信任與脆弱的交會中,慾望不是禁忌,而是連結的起點。
這個對話在當下的台灣格外有意義。2025年同志大遊行前夕,「手天使」宣布退出協辦,原因是主辦單位預計刪除象徵「性權即人權」的紅色宣言。手天使在聲明中引用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的自由,即「性自主權」,屬於人格與尊嚴的一部分。這場爭論讓人再次意識到,儘管台灣以婚姻平權自豪,但當討論轉向慾望、身體與性實踐時,自詡「文明」而「乾淨」的主流社會仍顯得遲疑。性權議題再次被邊緣化,而障礙者的情慾與親密關係,更容易在公共論述中被抹除。
在這樣的時刻,林海暎的書提供了一種重新思考「性」的方法。她沒有把性視為行為或道德問題,而是一種「關係」、也是認識社會的方式——「以性作為方法」的觀點。透過受訪者的身體經驗,她看見儒教父權體制下「保護」與「羞恥」如何同時運作,並看見障礙女性如何在縫隙中創造微小的自主空間。這些故事讓我們理解,親密不只是兩個個人之間的情感與互動,也是一場與不特定多數人、制度文化、意識形態的協商。
對台灣讀者來說,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她者」的見證,更在於反觀我們自身。當我們自認「進步」時,是否也仍以「理性」、「安全」、「防暴」等語言迴避身體與慾望的議題?或弱者化、幼稚化自己無法想像的情慾主體?是否仍無法正視性權作為人權的一部分?在這些問題上,台灣與韓國、香港其實共享了一個類似的東亞脈絡——儒教的家父長文化、對女性貞潔與障礙的雙重規訓、以及國家對「適當性」的隱性審查。
《我也想要愛!》以嚴謹的學術方法與具有倫理關懷的「看見」,讓我們留意到那些在「受限」而被期待「自律」的身體,如何仍努力尋找愛與被愛、慾與被慾的可能。它與《幽黯國度》、《十年前,我們的殘疾情事》共同構成一條東亞的知識譜系——從研究到行動、從書寫到實踐——提醒我們,性並非私密邊陲的議題,而是個人如何編織社會、建築公共的核心基礎。
當我們學會從身體出發,不再把差異視為距離,而是理解的起點,也許我們就能重新想像「關係」與「親密」的意義。屆時,性不只是慾望的某種時態,更是社會正義的語法。
中文版推薦序一
性作為方法——從身體出發,重新想像親密、關係與性權
李柏翰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理事
受訪的智能障礙女性J回憶起她青春期時摸索身體的經驗。她有點靦腆地說:「有時候摸到太酥麻就會叫出聲音,完全不由自主。」那句「不由自主」帶著難以掩飾的羞赧,也產生一種確認自己仍然活著的感受。另一位受訪的視覺障礙女性D提到,她從國中時期開始會聽色情錄音、試著探索身體的反應,即便如今有了伴侶,偶爾還是想「自己來」,因為那是能「取悅」自己的最佳方式。對她...
作者序
【前言】
重新思考「不同」
在《莊子.齊物論》中,有段關於美人的描述是這樣的:「魚看見她就潛入水底,鳥看見她便振翅高飛,鹿看見她則拚命奔逃。」
上述內容的意思是,即使是人人稱頌的絕世美人,但從魚、鳥、鹿的視角來看,卻不是「真正的美人」。對牠們而言,人類哪怕是再美,或許與其他人類都一樣,都可能是威脅自身的可怕之物。
以單一標準認識萬事萬物,其實是將「相同」的框架強加在認識之上。而這種同一性,往往會將那些擁有「不同」特質的族群貼上標籤,使其成為被劃界的對象。
既然如此,那麼在同一性內的認識,稱得上是真正的認識嗎?或許,意識到「不同」的存在,並且理解蘊含其中的多樣性,進而使這些多樣性以百花齊放的方式綻放,會不會才是更開放的理解呢?
從事社會福利學的教學工作將近二十年以來,筆者經常從人們的口中重複聽到某些話。其中之一,便來自於筆者在撰寫本書時,與障礙女性訪談互動的經驗。
在我們見過幾次面後,她大概認為彼此比較熟悉了,於是笑瞇瞇地對我說:「因為您是大學教授,在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也很知性,所以我一直以為會是個苗條的人,哈哈哈⋯⋯結果發現您就像鄰居大姊一樣親切又溫暖,真是太好了。」她在說出這番話的同時,也悄悄觀察著我的臉色。於是,筆者也以尷尬的幽默不動聲色地帶過:「因為我長得比較圓潤,所以才會讓人覺得像鄰居大姊一樣有親和力又沒壓力吧?」她聽完後,立刻露出燦爛笑容,並回答了一句「是啊」。
這段經歷讓筆者不禁開始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根深柢固的隱性偏見往往是如此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其實,如果更坦白地說,筆者的心中也同時浮現了一個疑問:「為什麼當下的我沒辦法機智地反應,即時拆解那種刻板印象,反而選擇以似是而非的親切感來包裝成幽默回應她呢?」
隱性偏見又為什麼會深植於人們的心中,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表現出來呢?像筆者一樣暴露於刻板印象之中的人,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才會把矮小、豐滿的外貌包裝成「親切」的形象,藉以作為緩衝機制呢?
像筆者一樣矮胖的女性,最常聽到的貶低評論是「疏於自我管理」、「吃很多」、「懶惰」等。於是,肥胖的人很容易僅因外貌就引起反感。鄭熙真(2013)認為:「在我們的社會裡,女性的體重不僅是節制與忍耐等自我管理的指標,更早已成為女性人格與認同的標準。」因此,她主張「女性的體重是直接威脅就業、婚姻、人際關係、自尊感的生存問題」。倘若一個人因為肥胖、長相不佳,再加上像筆者一樣體型矮小,而無法被歸入「好感」的類型,那麼這個人就會成為例外、異類,甚至是低劣的族類。如果用更極端的表達方式,那就是明明是女性,卻淪為難以被接受為「女性」的存在。
在筆者的潛意識裡,或許也默默藏著對「淪為不起眼存在」的莫名恐懼吧?在我們的社會中,任何偏離標準、平均範疇的人,很快就會被加上或優或劣的評價,進而被分門別類,貼上標籤。舉例來說,任何置身現今韓國社會的成年女性,只要體型屬於偏離平均的肥胖、矮小,就算擁有專業,也會成為嘲笑的對象。在被貼上特定標籤、與符合標準的一般人劃分界線的那一刻起,無論兩者的差異明顯或細微,他們都很難再與「某方面有缺陷」的觀念脫鉤,最終只能面對受人歧視與自我貶低的悲哀現實。
從某種層面來說,或許正是因為筆者很快就在有意無意間察覺到如此悲哀的現實,才會發展出這種自我保護機制。只要平均、同一性等肉眼看不見的社會標準始終像銅牆鐵壁般在這個社會牢固地運行著,那些與「我」不同的存在、無法被歸類為「我們」的族群,就只能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存在。原因在於,「同一性」這個標準,是許多刻板印象用來劃分界線、並對界線之外的部分加以歧視的手段。
假如連非障礙女性都會在日常生活中飽受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那障礙女性又會面臨什麼樣的處境呢?與非障礙者有著不同的身體及精神結構、機能、發展的某些障礙者,像是肢體障礙者、腦性麻痺患者、智能障礙者、腎功能障礙者等,因為被冠以關於「障礙」的各種稱呼,她們有時會被人投以不必要的關注與同情,或是必須面對自己未必願意接受的過度善意。再加上,可能連她們的存在本身也會令眾人厭惡、憎恨,彷彿是染上可怕傳染病的人一樣,被整個社會拒於門外。障礙者時而被視為人類戰勝苦難的主角,時而被貼上可能犯下滔天惡行的危險人物的負面標籤,因此只能被迫處於邊緣化的位置。
在韓國社會裡,所謂「不同」而非「相同」的存在,意味著與我或我們相異的存在。這種異質的存在,不被認為是有自己獨特生活方式的個體,而是不協調、錯誤的,因此成為了不正常的存在。於是,這些人只能成為我們透過電視劇、新聞、電影接觸的無名氏,而不是與你我一起呼吸、生活的朋友或鄰居,否則就是日常生活中不願接觸與交流、讓人感到不適的族類。像這樣被劃清界線的障礙者、障礙女性,在無形之中成了被歧視的對象,無論這種歧視是善意或惡意。這些人彷彿只能在優越者施捨給弱者的寬容之中,成為必須仰賴他人慈悲與憐愛的卑微之人。這正是筆者想關注障礙女性的生活,以及她們在這種生活中如何展現性與愛的原因。
如果社會能認同有不同的存在,也就是異質的存在,那麼這些擁有差異的其他存在與族群是否就能擺脫被隔離、他者化或歧視的對象呢?如果我們認同擁有不同身體與精神的人,是理應一起生活的朋友、同事、鄰居,社會也予以關懷,為其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這些人是否就能作為擁有同等權利的主體,好好生活呢?
近來,為了改善社會對障礙與障礙者長期以來的負面認識,出現了一些旨在提升大眾對身心障礙的認識的童書,讓孩子從嬰幼兒時期就開始理解:「障礙」也是我們生活的另一種樣貌。像是作家鄭鎮浩(2014)的《往上看!》即是具代表性的繪本作品。
這個童話故事的主角,是名在家族旅行中因車禍而失去雙腿的小女孩秀智。秀智依靠輪椅生活,她的日常生活是從家中陽台往下俯瞰著像螞蟻一樣小的人群來來往往的景象。不過,從樓上往下看,只能看到人群又黑又小的頭頂。萬一遇到下雨的日子,更只剩下五顏六色的雨傘隊伍。直到有一天,一名路過的男孩試著向秀智搭話。當男孩得知秀智因腿部障礙無法下樓後,他二話不說就躺了下來,為的就是讓她看清楚自己的樣子。路過的人問男孩「為什麼躺在路上?」於是,在了解原因後,人們也為了讓秀智看得更清楚,開始紛紛躺在路上面向她。
這個美好的童話講述了一段暖心故事。人們為了因障礙而與眾不同的女孩秀智,透過集體的關懷,主動調整成她的視角,使障礙者女孩秀智成為能與非障礙者一起生活的朋友、鄰居。然而,當我們稍微轉移視角去審視這個溫暖、美麗的童話時,又會發現什麼事呢?這個童話故事仍然將因「障礙」而出現差異的個人、群體視為「需要非障礙者關懷、幫助的對象」。
非障礙者認同並努力適應「障礙」這項差異的態度,乍看之下確實是對障礙者的關懷與尊重。但由於判斷的標準是出自非障礙者的觀點,因此障礙者始終無法擺脫「身心缺陷」的傳統定位。於是,對身體與條件存在缺陷的秀智而言,人們溫暖的關懷依然停留在援助與慈善的層面。正因為如此,秀智俯瞰的世界與人們仰望的秀智的世界之間,終究存在著無法縮短的距離。
為了縮短秀智與世界的距離,必須在她生活的建築物裡裝設電梯,以便她自由地與世上的其他人認識、交流。雖然秀智依靠輪椅走路與其他人靠雙腳走路的方式、速度皆不同,但這些差異應被理解為「行走方式的多樣性」。
關於障礙女性的性與愛的記述不也是如此嗎?這個世界存在形形色色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因各自的條件與境況不同,而發展成對這個世界截然不同的體驗,但當這些體驗像彼此的鏡子一樣映照與敘述時,便在交流與共感之中變成栩栩如生的,我們的故事。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對於障礙與非障礙、正常、女性特質等傳統觀念與想法仍源源不絕地出現,偶爾甚至還會像虛構的神話般四處流傳。「性與愛」的議題,讓障礙女性在「正常」與「女性特質」等眾多虛構神話之中,必須毫無忌諱地面對真實自我,也是對世人展現她們的認知與行為的舞台。這當然也讓障礙女性不得不在冷酷的現實中,赤裸裸呈現她們的性生活與愛情生活。本書探討的是,身體構造、功能、精神特徵與非障礙者不同的障礙女性,如何因差異而招致歧視。換句話說,書中將分析使差異與歧視產生連結的緣由,並探索障礙女性在這種處境之下,如何在面對自己身體與女性特質的同時,理解與展現自身的性與愛。
【前言】
重新思考「不同」
在《莊子.齊物論》中,有段關於美人的描述是這樣的:「魚看見她就潛入水底,鳥看見她便振翅高飛,鹿看見她則拚命奔逃。」
上述內容的意思是,即使是人人稱頌的絕世美人,但從魚、鳥、鹿的視角來看,卻不是「真正的美人」。對牠們而言,人類哪怕是再美,或許與其他人類都一樣,都可能是威脅自身的可怕之物。
以單一標準認識萬事萬物,其實是將「相同」的框架強加在認識之上。而這種同一性,往往會將那些擁有「不同」特質的族群貼上標籤,使其成為被劃界的對象。
既然如此,那麼在同一性內的認識,稱得上...
目錄
中文版推薦序一 性作為方法——從身體出發,重新想像親密、關係與性權 李柏翰
中文版推薦序二 補上無障礙社會缺失的一塊磚頭——性與親密關係 郝柏瑋
各界推薦語 周月清、郭惠瑜
韓文版推薦序一 真誠聆聽障礙女性所詮釋的生命故事
韓文版推薦序二 她們是與我們毫無二致的,完整的人、一名女性
前言-重新思考「不同」
第一章 障礙女性的身體與性
有障礙的身體
被「女性特質」的傳統觀念禁錮的身體
以「保護」為名限制的性
名為「自律」的性主體
洞察界線與橫向思考
第二章 障礙女性詮釋的性與愛
渴望並且有能力實踐的性主體
幻想與現實的交會點
名為「暴力」的性
【總結】開啟全新的可能性-以橫向視角拓展障礙女性的性與愛
致謝
參考文獻
中文版推薦序一 性作為方法——從身體出發,重新想像親密、關係與性權 李柏翰
中文版推薦序二 補上無障礙社會缺失的一塊磚頭——性與親密關係 郝柏瑋
各界推薦語 周月清、郭惠瑜
韓文版推薦序一 真誠聆聽障礙女性所詮釋的生命故事
韓文版推薦序二 她們是與我們毫無二致的,完整的人、一名女性
前言-重新思考「不同」
第一章 障礙女性的身體與性
有障礙的身體
被「女性特質」的傳統觀念禁錮的身體
以「保護」為名限制的性
名為「自律」的性主體
洞察界線與橫向思考
第二章 障礙女性詮釋的性與愛
渴望並...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