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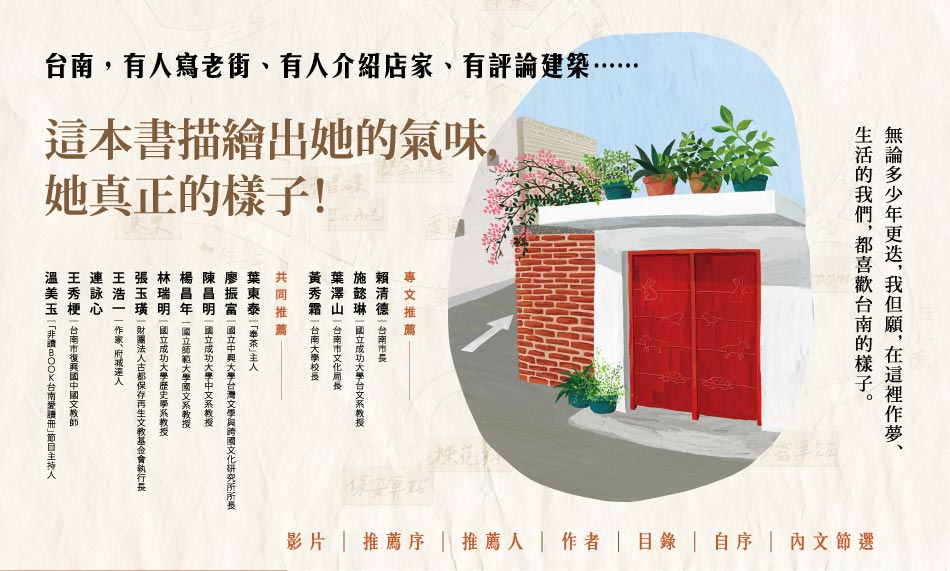




79折優惠價$253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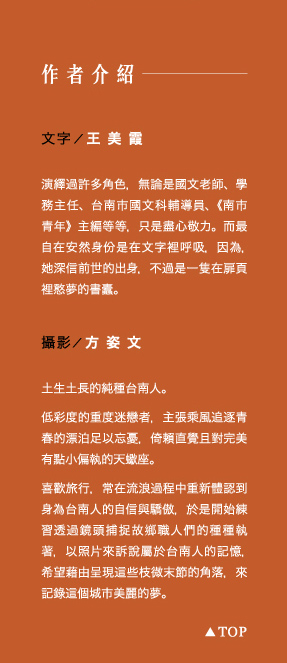


就是台南的樣子 ◎賴清德(台南市長)
文化源自於人類的生活,而生活又反映文化。台南,這座曾有三百年身為台灣首府的城市,走進它,就像走入台灣歷史,不僅在街道巷弄間,古蹟、傳統建築等文化資產俯拾即是,在人與人的接觸與生活中,更能深刻感受到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蘊。
甫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曾在一場題為〈這一路走來的我——從台南的土地談起〉的演講上說:「我對世界的眼光,是在台南養成的。我的紀律、道德標準,基本上是台南給我的。」台南的古雅氣質塑造了李安導演的個性。而每一位生活在這座被稱譽為台灣文化首都的人們,更是創造這座城市價值的重要角色。
自詡為文化志工的王美霞老師,在台南任教二十餘年,曾任台南女中國文教師及學務主任、《南市青年》主編等職務,在教育現場,她是第一線的尖兵,凡親炙受教的學生,有口皆碑,而她更了解,人文素養無論對個人的生活與生命,或是城市的競爭力與魅力,都深具重要意義。近年來,她開設文學與藝術的「南方講堂」,與一群文化界的朋友,積極推動各項藝文活動,讓城市的氛圍熱絡,從傳統的古色,走出年輕欣然的氣象。
近兩年多來,王老師走訪大台南地區許多深具特色的藝文景點,與負責的主人們深度對談,透過她沉穩深邃、清新婉轉的筆力,台南人勇於作夢、熱愛生活的氣象,盎然洋溢。王老師充滿愛的理解,帶著美的筆觸,寫盡台南人的生活款款,也寫出了在台南這座美好的城市,日復一日演出著「移居」與「宜居」的故事。
文化若可稱得上一種事業,也該是千秋事業,必須很多人長期一起努力,才得以略顯成效;文字的累積,不若數理科技快速,必須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的辛勤深耕,始得有收穫。欣見王老師兩年多來的文字作品即將出版,這也代表著一群鍾情於文藝工作的好朋友,在台南這塊土地上,不計報酬、長期努力的結果。推薦您可以打開這本好書,泡一壺好茶、帶著微笑,讀著台南古色依舊在,望向好未來的燦爛光采。
府城女子王美霞 ◎施懿琳(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中文系教授)
初識王美霞,在台北師大。印象中,我們似乎只曾在走廊匆匆照過面。我這個寡交友的丙班學姊,並未進一步與這位甲班的學妹交談,只記得美霞有一對略帶憂鬱的大眼睛。
再次見到王美霞,一直要到一九九九年。我從嘉義僻靜的一所大學轉到成大任教。南來不久,美霞託她台南女中的學生與我聯絡上了。沒想到當年偶然照面,竟種下日後彼此更深的緣分,在南方。
大眼睛依舊美麗,不過,眼底的愁翳已然散去。美霞聰慧俐落,樂觀有活力,行動迅捷如風,對各種知識資訊,掌握得周密而準確。腦子慢半拍的我,常跟不上她的節奏。她興趣多元,活動力強,尤其熟悉台南的人事物,總是熱心地要帶我去認識她的好友,參與她辦的活動。感謝美霞,願意耐下性子等待我這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書呆子跟上隊伍。因著她的帶引,讓我終於有機會,與她一起走逛老街,品嚐府城飲食風味……當然,這只是她豐富生活裡的片影。
台南女中退休後,美霞更全心全力地投入「南方講堂」的講學,而且與府城更多在地的人物密切連結。奉茶的葉老闆、吉他學院的劉老師,與美霞所組的「鐵三角」,在許多藝文活動場合出現。他們以無比的熱忱,輕鬆平易而貼近大眾的方式,唱著在地的歌,說著府城的故事,串連起台南人深厚的歷史記憶與美好的生活想望。每次活動,都讓觀者讚嘆,聞者傾倒。
不只動態的引介,美霞更透過她細膩而清麗的文字,把曾經熠燿生輝的活動化為精彩生動的文字。某些悠閒的午後,她會帶著相機,一一走訪台南的商家,與店家老板「談天說皇帝」;她深入府城巷弄,透過鏡頭與文字,讓隱蔽在一角,少為人知的宅居、庭園、奇人、異事……一一納入織錦般的美麗章篇裡。
而今,這些深鏤著府城印記的文章經過篩選後,即將出版了。作為「府城文化達人」的學姊,很榮幸有機會為這本書寫個小序。一方面紀念南來十餘年與美霞的一段因緣,也藉此向這位具有無限活力與能量,為地方付出許多關懷與愛的府城女子王美霞致敬。
寫給台南的情書 ◎葉澤山(台南市文化局長)
這是一本深情,有香氣的書。
在王美霞老師筆下,一字一字散步在風光旖旎的台南;執著誠懇的人們、古風流轉的城市容顏,沿途還飄逸著陣陣茶香、書香,與花香……。
讀《台南的樣子》,就像是一封封寫給台南的情書。
幸福的城市,品嚐幸福的味道 ◎黃秀霜(國立台南大學校長)
台南,是台灣最幸福的城市,幸福的味道在這裡。王美霞老師的新書《台南的樣子》記錄了幸福台南的點滴情事,恰似春風輕暖,總能令一樹花開,字裡行間交織著台南過去的成就與未來的希望。
台南有宜人的氣候,有深具特色的古蹟、老店、老街,有吸引人的美食小吃、自然環境,還有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一景一物、一店一人,訴說著動人的故事。美霞老師和我都成長於中部,不約而同工作於台南,定居於台南,而愛上台南。讓我們循著溫暖微風,跟隨美霞老師的步伐,發現獨屬於台南的味道,細細咀嚼台南的芬芳。
相信,不管歲月如何增長,台南依舊是你(妳)我心中最深刻的感動。台南是我們永遠幸福的地方!




在茶路上,走了多年,一日有個琴人告訴我,有人將他小兒對中文的學習熱忱拉起來了。我是知道的,琴聲須要是如詩的詞,同為人父的我,欣然的水正熱著呢!
幾回茶敘,這女子,細緻小巧可不安靜,話如花鼓,一陣前樂,才露和昫的化雨春風,再經過幾次的茶會,才知道她對教育的熱忱像古道上的馬蹄,漫漫長路,響個不停。
這次,女子將熱情投到台南各個有趣的角落人物,書店老闆、民宿主人、無菜單的餐廳夫婦、多個外地文青的台南夢、紅豆湯的漂流煮夫等等……。這些人正在構造一個新台南而動作不斷,說是春筍,似乎又成竹,甚至蔚成林。比較女子以往從古典文學獲悉的文化總成,是那麼不同,又似乎同樣的青猛。顯然就教育家的敏銳感觸,這有如大過紅樓夢般鮮活的府城夢,更超乎懷抱理想大夢的台灣人。
人生階段,各有巧妙,國文老師退休的女子,顯然才正開始編寫另外一部青春生命的教材。
職位可以退休,崗位可不然矣!——葉東泰(「奉茶」主人)
近年由於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機緣,常有機會到成大、台灣文學館參加各類學術活動。雖然幾乎每次都是搭高鐵匆匆來回,但台南的城市氛圍對我卻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美霞是我大學學妹,我們都是台中人,她卻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台南新移民,在這裡教書、生活、栽培下一代,體驗這座古城的美麗人情與現代風華。不知不覺,台南的基因已融入她的血液裡,滋養著她的生命,淨化她的靈魂。還記得去年五月,她帶我夜遊神農老街,穿梭在老宅院裡,與店家親切交談,並以驕傲的語氣對我細數老街的前世今生,讓我更直接感受到她對這座城市的深情。
美霞為了這本《台南的樣子》,已默默筆耕多時,想來這必將是我更細緻、深入品味台南的最佳指南。啊!生活在台南,生命多美好。──廖振富(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美霞是台南文化界的穿針人,她是最熟知台南文化底蘊的行家。當她從台南女中學務主任退休後,即成為台南市各種文化活動、會議的主持人,台南的文化人是她長年交遊的朋友,因此這本書,寫的是台南的人文景觀、市井風情,也是她個人的文化界情誼。
這不是一本導覽的書,也不是觀光手冊,而是一本浸透古都人情的小品,裡面缺少商業思考,卻飽涵台南的豐富人情。她寫茶行、園林、民宿、書店、美術館、咖啡館、藝術街道,背後都有人的故事。「奉茶」的葉東泰,不但懂茶,還有顆動人的心;「草祭」的蔡漢忠,不但是有理念的書店老闆,也是文化活動中,穿汗衫短褲,幫忙扛桌搬椅掃地換得一身涔涔汗水默默離去的義工;還有振發號的阿公、海邊的東東、鼎甲窯、衛屋、老塘湖、雙全紅茶、魚羊鮮豆……,一處處都是動人的故事。
美霞的序為〈就像花的樣子〉,是因為她以花開的心,照見台南的人情之美,如照花前後鏡,照見的是她內心世界的美,以及由此映現的,台南的動人身影。——陳昌明(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賢媛人師良為美
明文傳藝燦若霞
美霞宣揚文化功在桑梓新作問世欣撰嵌名之聯為賀
——癸己春 楊昌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台灣俳句:共生〉
台南的樣子
南都有自己個性
城市人共生
〈台灣俳句:花染〉
柔情逐綻放
花開老城有精神
顏色染身心
——林瑞明(詩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美霞老師花三年青春書寫台南,有感而說:「是人,讓風景美麗了」。
和她一樣來自外地,因著這兒眾多的美食、古蹟和老屋,近三十年來我亦樂以府城為故鄉。
然而說來汗顏,對台南的真美有所認識,不過是近十年的事。二○○五年基金會籌辦「台南建城二八○週年紀念系列活動」,與振發茶行老頭家嚴燦城、奉茶老闆葉東泰等有過深刻接觸,才慢慢地從幾位熱愛家園、樂於付出的老台南人身上,感受到樸拙心性和雍容氣度——這一幕台南最隱蔽卻也最感人的美景。
在當前一片瘋老屋、忙賺錢的潮流中,有度有心的老台南人,依然低調地守著崗位,不疾不徐持續傳布著古都的在地價值。——張玉璜(建築師/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常務董事兼執行長)
早年進行文史的田野調查,在訪談中,總覺得「人最美」。這座舊城的人們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戀」,有次演講,題目定為「美食,台南人在驕傲什麼?」當地聽眾的反應「預料中的好」,大家都很樂。其實,美霞老師在書裡所介紹這群可愛的人們,我認識,也深深地喜歡他們。他們在舊城裡活得很溫潤,在謙謙笑語中有自己「淡定的驕傲」,很美。
你問台南人,什麼好吃,他們總會說出一套自己的私房清單;你問台南人,什麼是歷史,他們說磚紅色的牆就在家屋和路間;你問台南人,什麼是生活,他們說曬一曬太陽,你就會知道。
台南的生活,他們用一把大提琴起伏,可以獨奏,也可以輕輕柔柔地伴奏,倚著午後慵懶的斜陽,巷弄的閒散長音,再搭著樹間風的輕快板,這就是他們說的曬一曬太陽。——王浩一(作家、府城達人)
我是台南人的子孫,很慚愧地在三十歲以後才開始熟悉這個城市。謝謝這本書,讓我更加認識台南的溫潤美好。——連詠心
台南真是好樣的。好樣的天氣、好樣的美景、好樣的小吃;好樣的情、好樣的景、好樣的人。只是,生活忙了,腳步趕了,我們常常忘了台南的好樣子,忘了它永遠都在。
美霞於我,始終扮演亦師亦姊的角色。好樣的美霞,當然寫得出台南的好樣子,箇中好味,留待您細細品嚐。——王秀梗(台南市復興國中國文教師)
這本書,讓我們得以窺見幾抹屬於這南方老城市特有的文明霞光。
結婚成了台南媳婦,忽忽二十年歲月纏繞著古城流轉,大大小小古蹟裡印著踩踏過的痕跡,氤氳的小吃攤滿是揮之不去的食物記憶。然,我如是以為,缺了台南的人情滋味,不是台南!千呼萬喚,美霞老師終於將台南如花、如詩、如散文涓涓滴滴流淌著的細緻與溫柔,透過日夜晨昏曾經的走訪,或安靜支頤品吟後的感知,以及與店家朋友的交心對談,慢工細活,琢磨再三,讓台南最為真實美麗如四季更迭的花,開了!
《台南的樣子》,如此貼近現場,卻又彷彿安靜不受干擾,在川流的人潮中,依然能夠悠閒地撫摸著斑駁歷史軌跡,自在地聞到茶香、花香與食物香,亦能輕輕地聽見擁有人文氣息的業主,如何在傳統與創新間平衡的聲音。前者來自於在地深耕的理想與祝願,末者則源自對己對人溫暖慈悲的情感與使命,於是我們有幸讀著、吟著歷史、地景、建築、美學、人文兼具且厚實的旅遊散文書。《台南的樣子》見證了真正的台南,不僅擁有歷史古蹟人文與傳統點心吃食,台南人溫厚篤實且樂天知命的氣味,亦是台南最美麗的風景之一。——溫美玉(「非讀BOOK台南愛讀冊」節目主持人)



推薦序
自序 就像花的樣子
輯一 黃花風鈴木
春天,忍不住的鵝黃,
在枝頭隨風一陣浪過一陣,
短促花期如夢,
瞬間,無蹤。
1. 府城的迎賓曲:奉茶、十八卯
2. 感情的生意,是尚嫷的花蕊:雙全紅茶
3. LESS IS MORE,海邊的陶淵明:東東園藝
4. 帶著紅豆去流浪:ㄇㄨˋ紅豆
5. 府城西、大市場,有謝宅
6. 靜靜甦醒的神農街:神農街
輯二 鳳凰花
如此底揮灑烈,
用一整個夏天,
燃燒紅與熱,
等待浴火重生。
1. 水鳥的歌聲輕輕飛揚:水鳥客廳
2. 大手牽小手的夢:懶人民宿
3. INART Space:藝術,不過是方圓之地
4. 城裡的房間:a ROOM
5. 等待飛魚的記憶:飛魚記憶美術館和木子
6. 鐵枝路邊的後花園:半日閒
輯三 菅芒花
色無香風來搖,
草原秋日,
夢清冷。
1. 在草祭的書香中:草祭、小說
2. 那一張包裝紙:陳桑
3. 法國香頌的探戈:有方公寓
4. 布的水,泥的山:鼎甲窯
5. 藝術清舞的遂園:方圓美術館
6. 鄰家的咖啡座:Tommy’s Coffee
輯四 水仙
迎來一朵花,
送走又一年,
花與時間在冬季交易容顏。
1. 在茶香裡看見你的微笑:振發茶行
2. 府城的京都驚豔:衛屋
3. 廢墟,是邊遠的夢:老塘湖
4. 咖啡,是另一種鄉愁:魚羊鮮豆
5. 城市裡獨特的高音:惟因唱碟
6. 捧一?溫暖的家鄉味:筑馨居
輯五 阿勃勒
牽起大手與小手,
串,再串,那明亮的黃,
要把家鄉土地灑成金沙鋪地。
1. 迷戀,黃色
2. 記得那個老下午
3. 衣服和女人的戀愛
4. 君子ㄟ批
5. 末日茶席
6. 華麗中的靜寂
輯六 楝花
1. 和你一起看楝花
2. 為了詩,再浪漫一夜
3. 圖書館散場的時候
4. 下午五點三十七分,沙崙線列車長
5. 我的牙科醫師
6. 永保安康的守候
店家資訊一覽



就像花的樣子 ◎王美霞
我喜歡現在的樣子,住在台南,每天像花一樣,努力生活、呼吸、認真過每一天。
葉石濤先生說過:「這是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夢、愛與結婚,都是花樣美麗的事。台南的春天,黃花風鈴木燦爛枝頭,很用力地野了一季之後,鳳凰花就豔紅紅地搶占灘頭;秋天,隨著水鳥遷徙來此,水光淪漣,白茫茫的菅芒花粉妝了大地,而勤奮的人們在冬季水仙花的祝福裡,送走現時的酸痛,期盼明春尚嫷的花蕊。在這裡,他們作著阿勃勒似的黃金夢,也像楝花,靜靜地開,靜靜地美麗。台南人,是落地的種子,一枝草一點露,就要努力長成美美的樣子,所以,在台南,要用花的容顏來記載節令。
我在這裡,擔任中學國文老師二十餘載,歲歲年年送走許多孩子駝著夢想的行囊,負笈他鄉。離鄉的孩子,緣於深深淺淺的鄉愁回來了,他們會以一種驕傲的心情告訴外地的伙伴,台南是文化古都,而每一次,我問道:「你帶他們去哪裡逛呀?」孩子衝口而出:「花園夜市……喔,還有,吃棺材板」、「然後呢?」接下來總是一片困窘的靜默。我分明知道,台南的美,不只這些,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分享呢?在教育窒息的體制下,孩子把一生中最美麗的十二歲到十八歲,浪擲在「學校、補習班、家」這等邊三角形的區塊裡,那美麗的古牆,那每間老店裡,馥蘊人情味的故事,與百年老店堅持的精神,都被匆忙的腳步忽略了。
二十多年前我從台北調職到此,台南,豔陽高照,鎮日熟絡的互動,那是充滿人情的,異鄉的我以「大抵心安即是家」的心態,逡巡品味這個歷史的城市,許多沒課的下午,我在一間間店家讀書、改作業或者寫作,那充滿光影的窗口,簡單的座位,以及時時有著花朵綻放的小空間,讓我熟悉了台南慢活的呼吸。漸漸地,我和店家主人熟了,他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讓一個個空間變得有意義。我一直覺得「是人,讓風景美麗了」,這些店家主人的生命理念,讓每家店都有了生命的景深,遍地開花,也讓城市美麗了。
我並不願意當我年老時,我們的孩子沒有故鄉的記憶,我更擔心沒有過往的人情味與夢想,會使得未來世代趨於寡情淡漠。所以,從二○一○年起,我開始在全台南市國、高中生都會訂閱的《南市青年》撰稿,每個月一篇文章,介紹台南人文風華,我想把台南每個景點、每間老店,那些可愛的故事,那些值得敬重的堅持,一一說給孩子們聽。連載三年來,漸漸有一群孩子,或者是爸爸、媽媽,會拿這本雜誌,去尋那些老店,點一杯茶、咖啡,或者買一?紅豆湯。我相信,如果在孩子年輕時告訴他們這故鄉的夢與美麗,時間久遠了,他們也不會忘記,到老了,拿來下酒,會有一盅滿溢的香濃。
撰稿至今將近三年,台南的大環境漸次酵化改易,這段期間島內移民增多了,文創的賣點花俏了,書寫台南的旅遊書,琳瑯書架,選在此時出書,一來肇因於一群好友與長輩的催促,二來是有感於每間店家,都是一個有理念的人經營的藝術品。人,永遠是台南最美的存在,是他們,讓一切豐足美好。我寫店家,親自與這些好朋友一一談心,他們的故事與愛,讓這些店具有意義,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裡,最美的花朵。因此,我願意用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樣子,來記錄他們,這也是我這本書最誠摯的初衷。
文稿集結成書,是為完成一份典藏的心願,感謝在訪寫過程中,以鏡頭與我相隨的姿文老師,她的畫面凝定了人與空間的永恆;也感謝「南方講堂」的好朋友,在你們的千呼萬喚中,我方能勉勵而為,讓此書呈現;更感謝我的那群好姊妹們用真情相挺;至於為我寫序、是我生命中亦師亦親的朋友們,我以感恩的心,領謝盛情;振筆的歲月,孜孜矻矻的日子,家人是我最溫暖的臂膀,感謝有你們,這本書,是寫給大家的禮物。
有一位愛台南的朋友曾寫道:「我會永遠記得你美麗的樣子,也請你永遠記得,自己的樣子。」我覺得那是每個愛台南的人,真心想說的一句話。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無論多少年更迭,我但願,在這裡作夢、生活的我們,都喜歡台南的樣子。


【內文節選一】
歲月的包裝紙:陳??
一張包裝紙,
靜靜地睡在歲月的櫥窗,
那是林百貨的美麗故事。
那一方地是父親的遺願
神農街的盡頭,藥王廟右轉,拐入一個S路底,鄰近民族路那一頭,有一字體純樸可愛的招牌,高高立在牆頭,書曰「陳??」。不起眼的小小方形看板,很難被注意,但是,這座民宿卻是建築新銳獎得獎作品,負責規劃的是大山空間設計,屋主是離家十幾年之後返鄉定居的陳怜怜及其姊妹。
陳怜怜的父親曾就讀於日本京都大學,攻讀化學工程,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務,退休後,轉任長榮大學教授及代理校長。由於自小家教甚嚴,陳怜怜自小對於父親有很深的敬畏感,負笈離家並到異地工作之後,對於家,一直保持著遙遠的距離。直到父親辭世前,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她毅然結束生醫科技的工作,回到家鄉。「直到那時候,我才又開始認識自己的故鄉,」陳怜怜說。父親辭世時,最放心不下的是這塊地,由於長年的產權不清,他很擔心一旦撒手而去,地產就沒了。不諳法律的陳怜怜為了使父親安心,決定擔起責任,承諾父親一定會好好處理這塊家產。之後,勘界、劃地、拆除藩籬、翻修房舍,在一步步整理屋舍的過程中,她看到父親終其一生留下來的寶貝:祖母的助產士醫藥箱,裡面有祖母的慈祥面孔;廚房的菜櫥,那是祖母的嫁妝,還有小時候在那裡鑽來轉去聞到的飯香;協進國小幼稚園的書包,是跳躍快樂的童年……。這一切切生命中難忘的印象,就在這些骨董的寶貝裡,顯得多麼有意義。於是,她決定用最大的可能,保留父親的土地與收藏品。就在這樣的決定下,老屋再生的民宿,誕生了。
珍惜老物件的愛
民宿改建的工程試圖還原父親生前慢活的生活氛圍,舊紅磚、舊木梁保存了台南建築的在地個性,空間以新與舊的和諧對話,充分借景,保留了巷弄內居家的閒散情調。穿梭在「陳??」的空間裡,六十年歷史的家具與記憶,搭配亦新亦舊的風格。建築的新生命,是一種美好的延續,而在記憶與當下之間,隱藏著女兒對於父親與家族的溫厚情感。
「陳??」的櫥窗,是一個珍貴的寶貝盒,有祖父陳?就讀東京藥學士證書,林百貨包裝紙、上課用的課本、打毛線用的針線盒、不同時代的添炭熨斗、愛國婦人館的背章……,打開它,彷如走入一部時光機,那些令人驚嘆的老物件,一件件都可說上一段老台南的歷史與故事。這個櫥窗簡直就是小型的民俗博物館。陳怜怜說,整理這些東西時,她會想起許多家族的舊事。她的祖母,附近的人都稱「美仁官」,是通街巷的人都認識的助產士。小時候,當她在街頭街尾蹓躂,別人就會叫她:「啊!那是美仁官的孫仔。」這條街前前後後的孩子,都是祖母接生的。她的祖父是藥劑師,目前家裡還有藥單可證,讀幼稚園時,祖父常帶?她到附近廟埕串門子,陳怜怜一直覺得他是很好命的阿公。兩位老人家生前用過的東西,父親都一一收藏,現在才能提供分享,她真正打自內心佩服父親的細心與遠見,也在那些物品中,她好像慢慢懂得了父親的內心世界,並藉此超越時空與父親對話,與家族對話。「那種感覺,讓我知道自己是與父親很親近的,」陳怜怜很有感觸地說。「陳??」是她很重要的生命轉捩點,透過這個課題,她撿拾家中的記憶,每一觸及,就更深刻珍愛家中曾留下的一草一木,以及父親不曾言宣的愛,她覺得「陳??」是父親留給她最好的功課。
主人滿滿的隨緣情
離開「陳??」時,已近黃昏,陳怜怜送我門出門時說:「『陳??』的夜景更美,下回要記得來品茶。」語畢,還送了我們一袋台南百年老店的點心,她說:「老台南人的熱情,是不會讓客人空手而回的。」我曾問她,這麼好的民宿,怎不做廣告宣傳?她笑了笑說,提供民宿是認識朋友,隨緣就好。我喜歡她這樣慷慨、又很磊落的分享情誼,她以及她的「陳??」,註解了老台南人溫溫厚厚生活底?。
【內文節選二】
和你一起看楝花
今年楝花,又開了。花期初綻時,正好女兒維維回台南,所以,我和她去走一趟,靜美的花之路。
楝花一直和母親的記憶,是相聯繫的,我記得母親生病的那一陣子,我正為學務的行政忙得不開交,有好長一段時間,下了課,處理完公務,就搭車回台中看望她,那時母親總是心疼我如此奔波,拖著疲憊病痛的身軀還急急催我:早點回台南去。母親是聲音柔細的女人,為了急催我起身,那微細的聲腔就轉成一種尖調,像飄過眼前的風笛,我一向不知如何回應她,因為,每一次都捨不得搬離腳步,每一次,卻又礙於車班,只好匆匆走了。好長一段時間,母親就這樣安於我一次次的離去……。
記得那年暑假八月時,我又去台中陪伴生病的她,因為第二天要開行政會報,不得不夜裡走人,臨走時,已經是最後一班高鐵火車了,我握著母親瘦癟的手,伏在她的耳邊說:「媽,我回去了……」,母親從迷迷濛濛的病痛與昏睡中醒來,睜開眼睛看著我,她因病痛所苦,說不出話來,只是看著我、看著我,然後用很大很大的力氣抓住我的手掌,我驚訝於平生瘦弱的她,為什麼使出這麼大的力氣握住我的手,就在那一瞬間,我完全明白了她的痛!她唉唉地受著胃癌的折磨,說不出來,捨不得女兒又回去了,她也說不出來,所以只用狠力握住、握住,我的手。我的淚,在那一瞬間,滾了下來…母親與我對望一眼,然後,她放了手,氣若游絲的說:「回去吧,太晚了……。」
那夜,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搭上高鐵,又是如何從高鐵開車回到台南的家的。一路上,都是淚,像雨一樣拭不停,我悲傷地質疑自己:為什麼我只是女兒!出嫁那一年,父親不顧我的憤慨與反對,一定隨從禮俗對著開出去的新娘車潑水,母親沒有阻止是因為她一直相信:女人的命是隨婆家去造化的。我不知道那夜母親緊握著我的手的時候,想起什麼?但是,她在往生前幾日,那樣緊握著我的手的力量,卻讓我一生難忘且不捨。
母親走後第二年,校園門口的楝花樹又開了,花開的時候,灑落了一地的淡紫,那是我走過母親逝去的悲傷後,第一次驚覺花又開。楝花來時,是淡紫色的煙霧,短暫的花期,讓人總在看它花開時,下一個瞬間,花便落了,更多的時候它都偽裝得像一株沉默的路樹。我一直覺得,它很母親,像我的母親,靜靜默默地兀自展演著她的人生,她的美麗。有天午后,我站在樹身下,仰頭看它,然後,一陣風把那淡紫的花瓣,像零落星子般吹下來,飄零的花瓣落在我的髮上、肩上,輕輕地,像母親曾經說話的聲音,那一剎那,我彷彿感覺到母親又回到的我身邊,同我說話。自此,我除了戀著油麻菜子花之外,也在楝花的夢裡,想念著母親的記憶。
去年,發現虎山國小附近的一片楝花樹林之後,每當春來,我便喜歡告訴周遭朋友:別輕易錯過楝花花期。
維維從台北回來度假,母女兩人閒閒地去逛市場、買菜,洗手做羹湯,日子在台南,曬得真是一派陽光且溫煦。女兒從英國讀書回來之後,成了最暖貼我這個阿桑的伴,也許是在女兒去英國這一年,我從失去母親的際遇中,明瞭女兒永遠最像媽媽的,所以就更綿密地守著兩個女人的祕密,記得前一陣子去台北,看賽德克巴萊的霧社戲街,淋得滿身是雨,滿臉蒼白,在火車站搭車回台南時,女兒等在月台,不肯先走,我跟她說:媽媽可以啦,她卻開始覺得媽媽已經需要人照顧了。我很健壯地告訴她:「阿桑還沒老去喔」,她仍舊頻頻回頭,一臉憂慮。
我教她做菜,她的笑聲永遠最大,像扮家家酒一樣,然後,把魚「丟」進鍋裡的尖叫聲,響徹雲霄,「菜是這樣煮的嗎?像作戰一樣!」我問她。
她倒反問我:「怎麼學會做菜的?」我真的忘了,因為,我的母親不善烹飪,每次家中有客人,是我親自操廚,也許,我是像李白夢中得五彩筆一樣,突然有一天夢裡的高人給了我一個鍋鏟吧。
午后,我問維維去看楝花好不?
那一段路,我常常獨走,因為是思念母親的楝花之路。驅車前往,有人在樹林中拍婚紗,楝花果真開了,但淡紫紫的茫茫,行走其中,滌盡煩塵。
我們慢慢地走著,我想起很多女兒小時候的事,有一年在英國劍橋,我們發現香蕉冰淇淋太好吃了,就一人一筒嘴饞地舔得很忘我,坐在我們身邊石凳上的英國男人看著我們的饞像覺得很好玩,就問:「Are you sister?」我和維維都楞了一下,然後,我很鎮定地說:「Yes,We are.」至今,女兒仍調侃我當時美麗的謊言。
我常想,人生路上,有許多祕密是每個人橐著的囊袋,無人能知、能懂,甚至,永遠緊掩。也許,我該趁著記憶仍未褪去之前,一一記錄這些笑與淚。母親在她七十餘年的人生中,一直不善於表述,愛,而且,甘心忍受的苦太多,她的生命如楝花淡而來,淡而去,所以被忽視太多。如果,我的知識與教育讓我與前一代的父母不同,我想最重要的改變就是:讓下一代懂得走向楝花,欣賞花般美麗。總有一天,我也將與世界告別而去,那麼,當每年楝花開時,我想他們會從我的敘述中知道:母親,有一雙手,是很愛孩子的力氣,就像我的母親當時緊緊握著我一樣。


| ------------------------------------------------------------------------------------------------------------------- | |||||||
| 延伸閱讀:台灣味.深情旅遊手札 |
|||||||
|
《最絢麗的黃昏過後》
|
|
《小地方:一個人流浪,不必到遠方》
|
|
《GO!畫筆丟進背包裡》
|
|
《愛吃鬼的祕徑》
|
|
|
日本知名紀錄片導演林 雅行,用心記錄九份、金瓜石凋零的礦山榮景與礦工故事,以及兩地的優美風光,這是他「著滿懷的愛情,獻給隔鄰親切台灣人的一本書」
|
因為情感,她選擇回到原鄉-台灣,用二個四季行走於島內,寫下每個小鎮的景與情,24個節氣24種心情...
|
帶著一隻畫筆,走訪、畫下台灣最質樸自然的小地方-瑞芳、九份、北濱;用最簡單的方式,喚醒了心中小小的創作渴望…
|
作為遊玩的嚴選品牌──李昂
帶你體驗台灣的另類漫遊,吃非一般的全台美食,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快樂,真的可以從很小的事情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