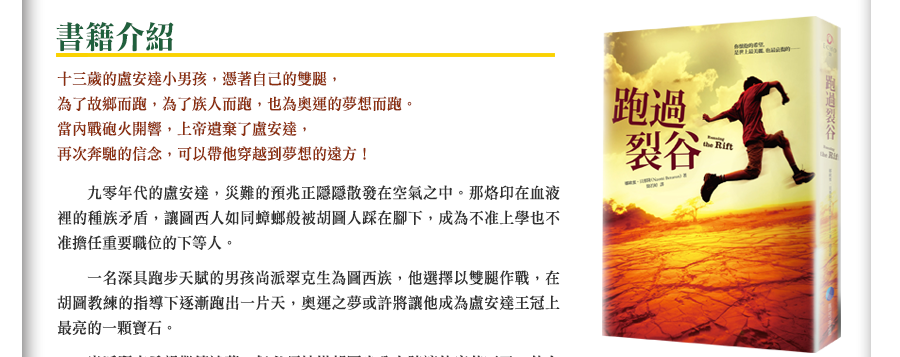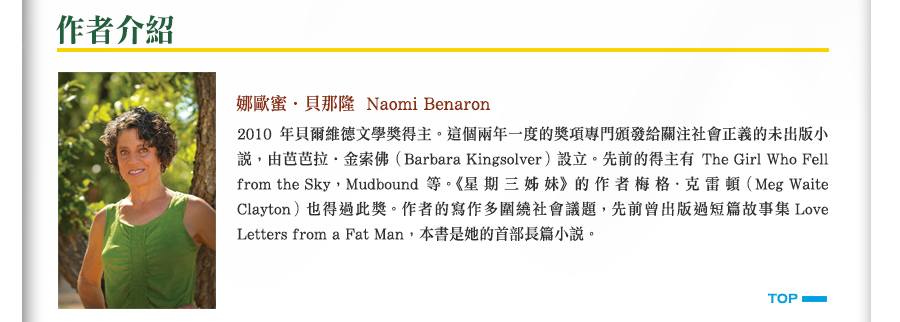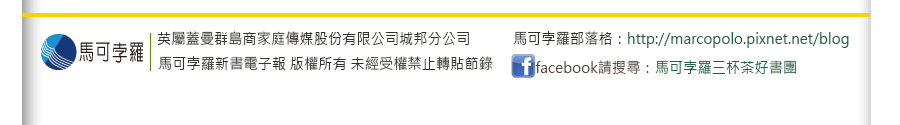一九八四年
第一章
爸爸開了房門走近床邊時,尚派翠克早已醒了,正在傾聽外頭的狂風暴雨。雨絲唰唰地刮著窗戶,咚咚地擊打屋頂波浪板,尚派翠克挨近哥哥羅傑取暖。這會兒他想起來爸爸要去吉佳利參加一場研討會,爸爸說過那是很重要的會議,盧安達全國各地的教育界人士都會出席。
「我要出發了。」爸爸用勉強壓過雨聲的音量悄聲說,「尤威曼納馬上要來接我。」尚派翠克心想:如果連校長都要去,這場研討會可真是超級重要的。
提燈的火光熠熠地映在爸爸的眼鏡鏡片上,也照亮他白襯衫的一片三角形區域;一定是暴風雨又造成停電了。「你們兩個男生把牛趕進圍欄後要仔細檢查門有沒有關好,別讓大雨把土壤沖走了。」他把他們肩部的毛毯掖緊,「還有羅傑──你要負責檢查尚派翠克的作業,我希望你們兩個的作業都別有錯誤。」
尚派翠克轉開臉迴避光線,偷偷皺著臉扮個怪相。他才不需要羅傑檢查他的作業呢,就連爸爸都很難在他的作業裡找到錯誤。
「我明天晚上就回來。」爸爸說。
尚派翠克用手肘支起身子,看著爸爸循著黃色光束走向走廊,腳步聲踏在水泥地上發出回音。「爸爸,祝您平安,」他說,「願伊瑪納保佑您旅途平安。」十一、十二月的雨季名為「蓋休勾羅」,在這個時節裡尚古古的聯外道路經常化作一片泥沼,有時候尚派翠克走在這條路上,會陷進深及腳踝的爛泥巴裡。
雨下了一整天,暴漲的溪流傾瀉流入基伏湖。山坡上沖下飽含紅土的洪流,尚派翠克放學回到家時,褲管已經被泥巴染成了鐵鏽色。他寫完作業之後,拿出玩具卡車在客廳裡玩,這車子是他爸爸用衣架、木塊、鐵片和色彩鮮艷的塑膠片做成的。
羅傑有一只錶,是「穆足古」(白人)傳教士送的禮物。他不斷重新設定鬧鈴時間,放在尚派翠克耳邊讓它嗶嗶叫。他們父親任教的吉漢威中學裡響起放學鐘,建築間迴盪著學生們的談笑聲,源源的話語聲被雨聲攪得模糊一片。尚派翠克想像自己有一天從小學畢業後,也能成為那群學生中的一員,跟著他們一起高聲喧鬧。有時這種想望會強烈到近乎發燒的程度,讓他感覺時間變得無比緩慢,慢到滴答滴答的秒針每一下都敲在他的心上。
「我們還是出去趕牛吧,」羅傑說,「要是我們非等到暴風雨過去,爸爸回來時會看到我們還坐在這裡等。」
他們穿上雨衣和膠鞋,從屋側取了他們的長枝條。「我們賽跑過去。」尚派翠克不給羅傑回應的機會就率先開跑。
尚派翠克和羅傑之間的競賽是從今年開始的,因為羅傑今年加入了一個小型社團,開始在週末踢足球;這社團的名稱是「因足奇」──意思是「蜜蜂」。羅傑一有機會就跑步,好鍛鍊自己的體能、保持最佳狀態,而他經常會帶著尚派翠克一起練跑。他教導尚派翠克倒著跑的訣竅,以及如何擺動手臂和有力地踢步。
由於他們住在學校裡,爸爸借用一位住在附近的媽媽表親家來養牛。尚派翠克跑在馬路邊邊,因為那裡比較不那麼泥濘。他每天都努力想在羅傑追上他之前把距離拉開一點,但是今天他一敗塗地。不管他選擇什麼路線,雨靴都不斷陷進路面。後方吉漢威中學的紅磚牆都還沒被霧氣遮住,羅傑就已經追過他了。
尚派翠克隔著一段距離就看見那隻「因揚波」長角閹牛的弧形長角,牠是他們父親最愛的牛。在濛濛的雨勢中,那對大角在一小群牛的上方起伏轉動,恰似一位「因托」戰舞舞者的雙臂。他們走近時,閹牛抬頭看,眨眨水汪汪的黑眼睛。尚派翠克一隻手按在牛背上,感覺牠微顫的、濕漉漉的厚皮。在「因揚波」閹牛的帶領之下,牛群沙沙地動起來,走進由幾根搖搖晃晃的木柱圍成的牛欄內。
羅傑衝到吉漢威中學的大門前時,足足領先尚派翠克十步。他停下來脫下手錶。「你看──我們來回總共花了二十七分三十五秒,我計時了。」
尚派翠克大口喘氣,他的衣服、雨靴和雙手都沾滿泥巴。「你騙人,哪有手錶可以計時的,給我看。」他接過手錶,赫然看到粗體字標明的時間,就和羅傑說的一樣。
戶外廚房的炭爐傳來辛辣而濃郁的燉肉香,尚派翠克和羅傑快速剝掉雨靴和雨衣走進廚房。廚房裡的收音機正播送佩佩‧凱爾演奏的「蘇庫斯」非洲舞曲,帶有沙沙的電波雜音。尚派翠克的小妹抱著札沙里,隨著音樂跳「庫莎庫莎」舞步;札沙里的雙腿在她膝前晃盪。
「喔唷,賈桂琳,妳跳得好棒喔。」尚派翠克逗弄地說。
賈桂琳驀地轉身。「唉呀!你們怎麼搞的?是溺水了嗎?」她指著尚派翠克和羅傑腳邊蓄積的髒水。
羅傑從賈桂琳手裡把札沙里抱開,然後三人一起跳舞。尚派翠克模仿他從影片裡看來的舞姿搖擺臀部,正搖得起勁時,他聽到敲門聲,起初力道比較輕,後來愈敲愈大聲,直到他開門才止住那聲音。門外站著兩名警察,媽媽匆匆趕過來,她背後綁著仍是嬰兒的克蕾曼絲。
「我們非常遺憾,有個消息要通知你們。」他們說。
媽媽給他們端了茶來,背脊挺得直直的。克蕾曼絲嗚咽地哭了起來,媽媽把她抱起來安撫。札沙里坐在地上玩車子,好像這天下午和其他天的下午唯一的差別,就是有兩個男人來家裡作客。
那兩個警察說,他們一行共六人,全都是校長和學校主任。那輛運木卡車失控了──這是司空見慣的情形──下山的車速太快,載運的重量又遠超出這麼輕薄的卡車所能負荷。它轉過彎道時開到對向車道,迎頭撞上他們的座車。吉漢威的兩位代表都死了──包括尚派翠克的父親和訓導主任。另外還有兩人罹難,兩人身受重傷。這麼嚴重的事故中還有人能倖存,簡直就是奇蹟。運木卡車的司機幾乎毫髮無傷,看來很明顯是酒醉駕車。他還撞到一個騎腳踏車的男孩,男孩掛在握把上的一袋馬鈴薯散落在馬路上,警方找到了腳踏車,但沒看見男孩的蹤影,該處崖壁極為陡峭,在雨中進行搜救任務太危險了。
兩個警察咂著舌頭,感嘆像這樣死於非命的總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好人,是盧安達的未來希望。遺體現在在吉塔拉馬的醫院裡,假使他們許可,吉漢威的校長會帶他回家。
媽媽停下輕搖嬰兒的動作。「尤威曼納不在車上嗎?」
警察們說,這種特異的情形屬於伊瑪納展現神蹟的時刻,因為學校裡在最後一刻出了緊急狀況,校長就留下來了。「尤威曼納要我們去保健中心,等他太太打理好病患就接她過來。」
「安潔莉克。」媽媽說,她吐出這名字時伴隨帶著抖音的長長嘆息。「好──我想見到她。」
警察們站起來。「我們認識妳丈夫──真是個大好人。謝謝妳的茶。」
他們走了之後,媽媽直勾勾地盯著窗外,直到尚派翠克忍不住看看是不是有人站在窗外的狂風暴雨裡。他有些相信如果自己用力閉上眼睛,就能在眨眼間讓這個下午消失,然後抬頭一看就能看到爸爸剛結束旅程返家,一如以往帶回滿口袋的餅乾。
媽媽跪坐在他身邊。「別擔心,現在伊曼紐舅舅會負責爸爸的角色。」
「我討厭伊曼紐舅舅,」尚派翠克說,「他很笨,而且總是散發魚腥味。」
媽媽的耳光痛到他冒出眼淚。「你要對我弟弟尊敬一點,他可是你的長輩。」
尚派翠克再也忍不住了,大聲哭了出來。
媽媽把他擁入懷中。「我們要堅強,」她說,「想想你名字的含義:恩庫巴,你要和雷神一樣勇敢。」
門開了,安潔莉克走進來,身上仍穿著白色醫師袍。媽媽癱軟地倒在她懷裡。
到了午夜,雨停了,隱在雲層後頭的月亮像隻迷濛的眼睛。傍晚開始就陸續有鄰居和親戚帶著食物和飲料前來;吉漢威中學的學生和老師把小小的屋子都擠滿了;門邊有夜班守門人坐著喝茶。
擺食物的桌子安置在客廳裡,鋪著只有特殊節慶才拿出來用的桌巾。桌上放著幾盤糊狀的「尤加里」,配上有碎肉和魚片的燉汁蘸著吃;幾碗燉樹薯葉、綠香蕉和紅豆;油炸大蕉;水煮番薯和樹薯;還有嫩煎豌豆和法國四季豆佐番茄、一瓶瓶「普萊姆斯」牌啤酒與伊曼紐舅舅自家釀造的香蕉酒。安潔莉克不停手地烹煮食物,並端茶給媽媽、幫每個人擦眼淚。停電了,四周燭光熒熒,油燈在牆上投射暗影。尚派翠克、羅傑與安潔莉克一起坐在地上,將捏成小團、裹了肉汁的黏稠「尤加里」餵進克蕾曼絲嘴裡。
爸爸的書房裡透出一小塊光線,召喚尚派翠克走進去。書桌上的油燈將上了油的木頭桌面照映得好似柔軟的皮膚,爸爸的藏書環繞在他四周,撫慰了他的心靈。那些書的內容有物理學、數學和教育哲學。爸爸出發前一定在寫日誌,他的鋼筆擱在那本皮質封面的冊子上,筆蓋放在半滿的茶杯旁,彷彿他隨時會走進房間、拉開椅子,再次提筆書寫。尚派翠克將茶杯湊到脣邊喝了一口,突如其來的甜味讓他打了個冷顫。細碎的茶葉殘留在他脣邊,他用舌頭舔掉,品嚐他父親生前嚐過的最後滋味。房屋在夜色裡忽而呻吟、忽而沉靜。
媽媽過來找他,手裡端了一盤香蕉酒,那股甜膩、發酵的強烈氣味刺激他的鼻腔。「你累了嗎?如果你想睡就去睡吧。」
他搖頭,想著爸爸每到星期五晚上就會坐在椅子裡,邊喝香蕉酒邊吃花生,他幾乎能伸手觸摸爸爸嘴脣上閃亮的鹽粒。
「他一定在擬開會時發言的草稿吧。」媽媽撫摸著日誌的書皮說。
尚派翠克讀著內容。宇宙萬物都蘊含數學式:化學反應的平衡、葉片的費氏數列、兩個人類邂逅的機率。有件事很重要──句子寫到這裡就沒了,尚派翠克想像當時是樹叢裡有聲音,於是他爸爸放下筆往窗外望。此刻感覺上,好像不只是他父親的話,乃至於全世界都停住了,就像這未完成的句子。
那一刻,男人們都還在喝酒,有些人用同一根吸管喝著瓶裡的香蕉酒,女人們則還在重新補滿吃空的菜碗;那一刻,尤威曼納帶著棺木進來了。棺木後頭跟了一列爸爸住在魯亨格里的親戚,灰白色的晨曦從他們身後透進門裡。
「親愛的茱麗妲。」尤威曼納握著媽媽的手說,「不管妳需要什麼,都儘管向我開口,妳知道法蘭索瓦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群人排成一列準備弔唁,媽媽坐在棺木邊,她的家人和爸爸的家人都陪在她身旁。女人們哀慟號哭。
「你要過去嗎?」羅傑貼在尚派翠克身邊說。
「你呢?」兩人都不動。「我們可以一起過去。」尚派翠克說。
爸爸穿著一套沒看過的西裝,臉上有東一塊西一塊的深色瘀青,身體的角度看起來很不自然。尚派翠克不敢伸出手摸他。
「那已經不是你爸爸了,你爸爸在天堂。」有個小小的聲音說。尚派翠克低頭看到舅舅的女兒瑪蒂兒站在他旁邊,她把手塞進他掌心。「我姊姊死掉的時候,媽媽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本來在她這麼說之前我會害怕。我聖誕節的時候來過──你還記得嗎?你讀了一本書給我聽。」
尚派翠克當然記得。瑪蒂兒年紀小,對書本很感興趣,超愛聽故事。舅舅一家人來作客的時候,她會拉著尚派翠克的手直奔爸爸的書房。她會指著書架高處一本民間故事集說:「恩庫巴,唸那個故事給我聽,那個你的兒子米拉尤找到黎明少女米賽珂的故事。」她每次都要聽同一個故事。
尚派翠克不用朗讀複雜的文本,就已經對這故事熟悉到可以複述了。「有一天,妳會和米賽珂一樣,」他這麼說,「笑的時候從嘴裡灑落珍珠,然後妳的愛人就會知道他找到真愛了。」每次他這樣說的時候,瑪蒂兒都會咯咯笑。「看到了嗎?」尚派翠克會指著她的嘴巴說,「珍珠!正是妳的盧安達名字『卡瑪貝拉』的含義。」瑪蒂兒會再笑起來。
「你得跟你爸爸說你愛他,」現在她悄聲說,「他在天堂才會高興。」她踮起腳尖瞥向棺木裡。
尚派翠克看看羅傑,兩人一起湊近棺木,跪下來朗誦爸爸最愛的一段「傳道書」裡的文字。
「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那裡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那裡是你所必去的──」
尚派翠克嚥住了。如果他唸出陰間這個字眼,這件上教堂穿的襯衫會被淚水玷污。
葬禮當天,尤威曼納宣布全校停課一天,吉漢威中學全體師生都護送棺木到教堂。載滿乘客的汽車沿著街道開,後頭跟著步行的群眾。天空下著細細的冷雨,孩子們在路上追逐,泥巴濺在他們的腿和短褲上。
一隻棕鳶從樹梢飛離,尖銳的呼嘯聲在霧中縈繞。尚派翠克暗想,不知道爸爸的靈魂是不是也長著翅膀,就像教堂裡那些天使畫像一樣。基伏湖水面上起霧了,漁人們的身影在既不屬於水也不屬於天的灰色地帶忽隱忽現。青翠的山坡上有長角牛在吃草。送葬隊伍經過時,田裡的農夫們抬頭張望。有些人在胸前畫十字;其他人伸出手道別。
他們去的不是尚派翠克一家平常週日會去作禮拜的吉漢威小禮拜堂,而是去恩卡教堂,唱詩班的和聲與規律的鼓聲從敞開的大門傳出來。所有的長椅和靠背椅都坐滿了人,座位區後方還有許多人緊挨著彼此站立。在棺木上方,聖母瑪利亞的塑像眼中流出鮮血,灑在敞開的長袍上。聖母瑪利亞雪白的肌膚、受傷的心臟,結合迴盪的鼓聲和拍手聲,使尚派翠克心中充滿恐懼。他閉起眼睛回溯光陰,直到返抵他躺在暖和的被窩裡祝福爸爸旅途平安的時刻。他收回這句祝福,改求爸爸不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