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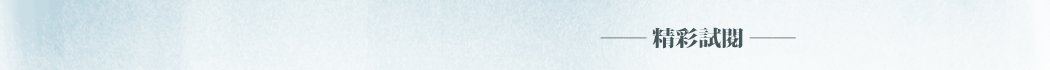
說來或許很難相信,但天賦異秉與生而殘障竟十分類似:孤立、神祕、嚇人。藉由研究我發現了一些模式,其中最驚人的是,很多人原先排拒異常,最後卻從中發掘到重要價值;同樣,很多人原先渴望優異特質,最後卻發現這些特質常讓人退避三舍。許多準父母害怕生出身心障礙的孩子,卻渴望孩子是資優生。這些孩子能為世界創造美好,有可能因成就非凡而擁有莫大的快樂,也可能讓父母的人生延伸出驚奇的嶄新階段。聰明人的孩子往往也聰明,但絕頂聰明卻是一種失常,一如本書中那些迥異於父母的水平身分認同。雖然心理學與神經學在上個世紀已有重大突破,但我們對於天才與神童的理解,還是跟自閉症一樣少之又少。天才兒童與身心障礙孩童的父母都一樣,他們得照顧孩子,但永遠無法理解孩子。
神童一詞通常強調時機,而天才則強調一般人所沒有的能力。許多天才並非小時了了,而神童也可能大未必佳。法國詩人雷蒙.拉迪蓋(Raymond Radiguet)說:「神童和超凡的人一樣,所在多有,但兩者鮮少相同。」不過在本書裡,我所接觸到的個案多是從神童一路延續成具備超凡能力的天才,因此我也沒有嚴格區分這兩個名詞。本章重點在探討一個人無論處於哪個階段,一旦展現異於常人的能力,會對於家庭結構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這就跟思覺失調症與身心障礙一樣,無論出現於人生哪個階段,都有影響。不過自幼聰穎過人與最終達成非凡成就,確實為兩種非常不同的身分認同。
撫養天才兒童就跟身心障礙孩童一樣,父母得配合孩子的特殊需求調整生活重心。除此之外,兩者也都需要尋求專家協助,而且一開始對應的策略也都讓父母力不從心。天才兒童的父母需求助於有相同經驗的團體,而且很快就得面臨是否要接受主流教育的抉擇:若把孩子送去智性程度相近的班級,與同學年齡就會差異太大而交不到朋友;若把孩子送去跟同齡孩子一起學習,則可能會因為表現太突出而被當怪人孤立。天才橫溢跟任何發展障礙一樣,都會阻礙親密關係,而比起書中提到的其他家庭,天才兒童的家庭也不會比較快樂或健康。
天才兒童擅長的領域中,最常見的是體育、數學、圍棋以及音樂。我把重點放在音樂天才,因為比起運動、數學與圍棋,我更懂音樂。音樂神童如何發展,全看父母能否配合。再怎麼天賦異稟,也要有人訓練,如果父母不支持,孩子就永遠不可能接觸樂器或的訓練。正如圈內專家費德曼與葛史密斯所說:「經營天才是一項團體事業。」
孩子的行為大多從父母身上學來的,反覆告訴孩子他以前如何,現在如何,將來可能如何,希望能同時保有成就與純真。在建構這些說法時,父母往往會把學得快與學得好兩者搞混。支持與壓力往往是一線之隔,而深信孩子有能力和揠苗助長,往往也是一線之間。無論是一味培養天賦而不顧人格發展,或是過於強調均衡發展卻忽略讓孩子最有成就感的天賦,都會毀掉天才兒童。孩子可能以為你只是愛他優異的表現,也可能以為你根本不在乎他有什麼才華。天才往往得犧牲當下,才能成就未來。若說社會大眾對於極度異常的孩子期望太低,對於天才兒童的期望則往往高過了頭,有害無益。
正如聾兒以肢體溝通,音樂神童也很早就開始用音調表達自我。對他們來說,音樂即語言。據說韓德爾在開口說話前早已會唱歌,鋼琴家魯賓斯坦想吃蛋糕時便哼起馬祖卡舞曲。音樂心理學家史洛波達專門研究人類為何對不同的音符與節奏組合有不同情緒反應,他寫道:「音樂和語言不同,不像英文那樣具有指涉意義。但音樂的確有多層次的複雜結構特性,類似於語言的句構和文法。」這表示,一如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所說,腦內深層的音樂結構一旦接觸外在音樂就受到刺激活化。紐約州巴德學院的院長伯恩斯坦幼時也是神童,他說:「要成為傑出的音樂家,首先得偏好以音樂作為語言之外的另一種溝通方式。」無論是口語還是手語,除了需要表達媒介,也需要有人接收、反應並鼓勵你繼續,這也就是何以父母的參與對於孩童的天賦展現至關重要。
即便音樂是孩子的第一語言,也不代表他日後能用得好,然而,只要這種語言能講得比一般美國孩子的英語流利,大家就把他們當成詩人了。
***
尼可拉斯.霍奇斯出生在音樂的世界裡。他母親是聲樂家,曾在柯芬園演出,為了家庭而放棄事業。尼可六歲開始學鋼琴,九歲以希臘神話的帕爾修斯為主題學習歌劇。十六歲時,他告訴父母自己想當作曲家,而不是鋼琴家。尼可說:「他們一副被我捅上一刀的模樣,我一直以為一切都是為了我,後來才知道都是為了她。那時我才驚覺我母親根本不在乎我想要什麼。」
隨著尼可長大,他與音樂的關係越發緊密,就越明白自己無法兼顧鋼琴家與作曲家的身分,而彈琴比較賺錢。他想「專心發展自己已經扮演的角色,而且好還要更好。」母親很高興。「於是我寫信告訴她,我再也不想跟她說話,之後我們一年沒聯絡。」現在,他所彈奏的大多是母親不喜歡的當代音樂。即使已過了廿五年,他表示:「那感覺幾乎像一個人出軌後,另一半很難完全忘懷失去信任這件事。當我彈奏十九世紀的音樂,她就會說:『噢!真好!噢,你確實喜歡這音樂!噢,沒錯,就是如此!』有次她來找我,我放了蕭邦的音樂,她就說:『噢!所以你還是喜歡蕭邦囉?』這就如同跟人說:『噢,你喜歡男生,但也還是喜歡女生吧?』她希望我能為她做點事,這便能滿足她。」尼可最後決定重返舞台,半是抵抗,半是默認。他說:「我回歸了她最初對我的計畫,但這次是我自己選擇的。在十六歲時突然讓她那麼失望之後,讓我更容易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
以音樂為志業需要極大的決心。鋼琴家魯道夫.塞爾金還在全球聲望最高的柯蒂斯音樂學院擔任總監時,有個學生告訴他:「我一直思考該去念醫學院,還是當鋼琴家。」塞爾金說:「我建議你去當醫生。」男孩回道:「但你還沒聽過我彈琴。」塞爾金說:「會問這個問題,就表示你當不成鋼琴家。」但下定決心當音樂家的人,仍應懂得質疑自己的決定。大提琴手馬友友雖然天賦異秉,神童歲月結束後,也考慮過從事其他職業。他寫道:「我的人生看似已然注定,但我非常希望有機會選擇。」他十分感謝父母,他們知道「天賦必須與發展成熟的情感相結合,才能創造出健康的音樂。」聲樂家泰瑞莎.馬勒是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的後代子孫,她也同樣慶幸未被逼著走上音樂一途。她說:「若是被逼,我或許會更成功,但我或許就不會發現自己有多需要音樂了。因為沒人逼我,所以我知道一切是我自己的選擇。」
神童經歷光輝歲月後,要決定放棄音樂,也同樣需要決心。卡普林斯基表示:「他們長大後,就很難清楚區分職業與自我。就算很不想當音樂家,也無法想像自己從事其他工作。」有些了不起的音樂家就是不想靠演奏為生。鋼琴神童范皇就告訴過我:「年輕時,成功看得著卻無法觸及。慢慢長大後,眼看距離想觸及的目標越來越近,才發現,那跟你想像得不太一樣。你在一片艱辛的大海中泅泳,每一件事都比看起來難搞,先前那個東西遠望覺得甚美,近距離一瞧才發現甚為粗糙且幾近崩解了。但你已經泅泳了這麼遠,也只能繼續游下去。」
***
野田健的母親野田貴代在《村聲》週報上看到鋼琴班招生廣告,便幫五歲的野田健報名。兩年後,老師建議她去參加茱莉亞音樂學院大學先修部的徵選。貴代一直想當名舞者,但她來自東京政要家庭,父親不讓她跳舞,因此藝術上她得不到的學習機會,她想讓兒子擁有。野田健回憶道:「突然間,母親開始坐在我身旁,看我練習,確認我一天練兩小時,如果犯錯就處罰我。我愛音樂,但我開始痛恨鋼琴,鋼琴是個不會振動、頑固又難搞的樂器,根本和打字機沒兩樣。」父母離異後,練習變得更痛苦。野田健說道:「怒吼不斷,簡直是場惡夢。天才兒童的父母,應該也要有個資格考試才對。我努力說服自己,她不是愛慕虛榮,因為她一天到晚跟人說她並非想當星媽。但她就是。我表現好的時候,她就充滿了母愛,表現不好時,就變得很可怕。」在這同時,Ken的父親等同於拋棄了他。「他常瞧不起我做的事,雖然並不是要針對我,而是針對她。因為我沒時間交朋友,又需要有人愛我,所以我拚命練習,如此她便會愛我,就算只是偶爾也好。你知道,我跟她之間有兩條臍帶,一條是大家出生時都有的那條,一條則是由音樂串連而起。」
野田健稱他的「第一份事業」起於十六歲,一九七九年他首次亮相,與指揮巴倫波因同台演出並大受好評,哥倫比亞藝術管理公司立即與他簽約。巴倫波因對野田貴代說:「他彈琴時,內心有好多的感情,有好多心事,但身體卻非常緊繃,幾乎要扭曲變形。我擔心他會傷到自己。」野田健拜巴倫波因為師,雖然磨練技巧很吃力,但他彈奏時卻有深刻的洞澈世情的悲懷。他說:「我有個老靈魂。」但靈魂再老,也需要青春的滋潤。野田健說:「我早早開始接受培養,接受塑造妝點,推上某條道路,不停拜見名人大師,十個裡有九個人看到的我,是他們一心想塑造的我。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讓人逐漸中毒,最後終於死去。」母親在他十八歲那年離開他的父親,投入一名義大利畫家的懷抱。「一切突然豁然開朗,我明白她自己也被困住了,只能把我當成她的出口。」
他廿一歲出櫃,為了心理健康,也為了音樂,他必須這麼做。他說:「年輕人喜歡愛情故事、戰爭故事、正邪對抗的故事與老電影,因為他們的情感生活大多十分絢爛,而且本該如此。他們把這些渲染過的情緒帶入表演,效果也總是動人心弦。但隨著人逐漸老去,絢爛的情緒不再新鮮。曾有段時間,我能夠描繪這種絢爛的生活,知道什麼叫失去、什麼叫失敗的愛情、什麼是死、什麼是狂亂的性。我曾有能力憑想像揣摩這些情緒,這也是才華的一部分。但這能力會逐漸枯竭,每個人都是。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天才在二十歲前後時陷入危機。想像力如果沒有人生歷練的澆灌,表演時就越來越無法重現這些情感。」
野田健與許多指揮大師合作演出,經紀人一年前就把他的行程排好了。廿七歲時,他遇到危機,險些自殺。「我喘不過氣來,彈琴變得小心翼翼,像是個有精神潔癖的人,一個音都不放過。我的音樂一直都很乾淨,但到後來,乾淨卻變成神經兮兮,無法傳達任何東西。」他去見了哥倫比亞藝術管理公司的總裁,表明要解約。他的經紀人說:「但你未來五年的演出都排好了。」野田健回答:「那麼我想取消我的人生。」十五年後,他告訴我:「那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興奮的事。」
野田健的存款夠他過上一段舒服的日子而且不用工作。「所以一整年間,我就在紐約走來走去。坐在公園內、上博物館、去圖書館──所有我以前做不了的事。人們問我:「接下來要去哪表演?」我總回道:「哪裡都不去。」那是我這輩子最棒的一年,因為我是誰、我有什麼價值,都跟我的天賦完全無關。」
隨後,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藝術總監詹姆斯.李汶邀請野田健擔任他的副手,健的第二段音樂人生就此展開。健負責訓練歌劇演員。李汶有點難以親近,野田健則溫暖開朗,打動了許多表演者。他說:「我現在的音樂人生就像一場美夢。我愛劇院、愛歌劇演員,我愛大都會。」他偶爾會參與表演,通常是上台伴奏,低調一點比較合他胃口。他表示:「上台只是要向自己證明,我不是因為怯場才停表演。」
野田健花了好幾年,才明白他的新事業與舊事業一樣累人。他每天早上五點前起床研讀歌劇,六點半抵達大都會,花幾個小時練習、排演、訓練,直到深夜十或十一點才回家。他四十五歲時感染葡萄球菌,急診醫師要他填緊急聯絡人,他赫然發現自己並沒有人想通知,於是陷入憂鬱。他感到身體內的音樂再次枯竭。音樂一向引領他往前走,維有當音樂衰微時,他才會發現底下的自己精神衰弱。「因為你每天都在重現這些情感,所以非常非常容易以為自己都經歷過。邁入中年後,我開始渴望人生,那些我在書上、電影裡或他人的家庭裡看到的人生。」
四十七歲時,野田健第一次認真談感情。他說:「以前談過很多場戀愛,都是有點戲劇化、像流星一樣一閃即逝的愛。終於開始認真過生活後,我變得很怕自己的藝術生產力消逝不見。」這種恐懼不時讓他想縮手。健說:「第一次和韋恩分手時,他心都碎了。三週之後,他回來找我。」健口中描述的這種社交障礙,是他經年累月孤立於世所造成的。某次同志遊行途中,他告訴韋恩自己要去大都會練習,韋恩說:「你是我的伴,不能就這樣離開。你不可以就這樣跑回歌劇院躲進練習室。」健告訴我:「我從小就未曾跟其他小孩一起出去玩,現在何必在四十七歲時跟伴侶一起出去玩?」不久之後,健把自己的鋼琴與琴譜捐出去。「回家沒鋼琴可彈感覺真的很好。」
野田健與父親疏遠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和父親重新往來。貴代也表示,她對於自己在健孩童時期的所作所為十分悔恨,而他們兩人後來也重修舊好。健說:「我無法遏抑對她的愛。我從不恨她,但這份情感實在太過強烈,我得奮力抵抗,才能找到人生的其他重心。」他頓了一下,又說:「我人生的驅力及重心,都來自母親的鞭策。她的鞭策讓我走了很遠。她給了我第一段音樂人生,而我恨那段日子,我永遠無法原諒她。但若不是有她,就不會有第二段我鍾愛的音樂人生了,這也是我永遠無法報答她的。」
***
雖然神童父母一旦嘗到名利的滋味,有可能轉為剝削,但他們多半不是真的貪財,只是沒有自我覺察,也沒有能力區分自己的期待和孩子的願望。小孩總能反映出父母的野心。如果你朝思暮想著生下天才兒童,就會在孩子身上看見天分;若你相信名聲能解決一切憂煩,你就會在孩子臉上看見他們對成名的渴望。雖然許多表演家非常自我中心,但最自戀的往往是神童的父母。他們將自己的願望、野心與身分認同建立在孩子的所作所為上,而非孩子本身。比起探索孩子是誰,他們更想追求名利。在我看來,他們有時雖顯得十分無情,但很少是因為懷著憤恨為之。他們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傷害,反映出他們對於兩個人生之間的界限抱持著可悲的錯誤認知。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而世界上擁有最絕對權力的人,就是父母。這些天才兒童的父母雖然極度關注孩子,卻又看不見孩子。孩子之所以傷心難過,往往不是因為練習很苦,而是因為不被看見。
